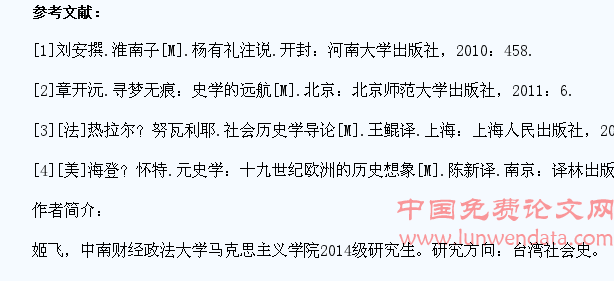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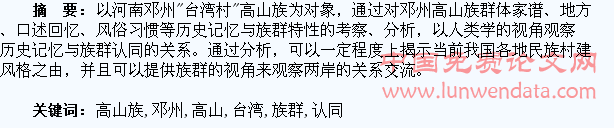
自2002年陈氏家谱《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被公开以来,位于河南邓州市的“台湾村”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台湾村”高山族历史记忆的探讨与分析,透视其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希望以此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族群问题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参考。
一、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与现状
邓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的高山族人口为946人,邓州市占有830人,其中,张村镇的高山族人口为609人。2003年6月,张村镇新建牌坊门楼,上嵌“台湾村”三个大字。“台湾村”即张村镇,根据家谱记载,相邻的文渠乡谢氏亦来自台湾,通常意义上,“台湾村”包括张村镇与文渠乡两地。
张村与文渠乡多为福建移民,故被称为“闽营”,福建人移居至此地与郑成功部将黄廷有关。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年,黄廷降清,被朝廷封为慕义伯,至康熙七年,应令到河南邓州开垦荒地。后应康熙令,于康熙七年往河南等地开垦荒地。由此可知,康熙三年黄廷顺清,被赐为慕义伯,并于康熙七年率部屯垦邓州。经过300多年,当初几位台湾“土番”的后裔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当下的“台湾村”。
1983年,张村镇上营村的陈朝虎成功填报高山族,后当地文化工作者涂征先后撰写《中原的“台湾村”》等文章,邓州高山族因此逐渐引起外界关注。自2002年起,八大家谱相继被发现。基于民族政策放宽、尊重民俗等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高山族人数量高速增长。至2005年8月,邓州“闽营”后裔有3074户13254人,而自报高山族的有544户2674人,高山族户、人比例分别达到了17.9%和20.1%。
二、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
关于历史记忆,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它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中以这个群体所认定的“历史”而在群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对往事的记忆。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情感产生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州高山族族群的重建与以家谱为代表的历史记忆的强化关系密切。通过考察邓州高山族已有的与正在被构建的历史记忆。邓州高山族的历史记忆表现为文献中的历史记忆、口述中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历史记忆三种方式。
(一)文献中的历史记忆
文献中的“历史真实”并不能十分真实地反映过去客观发生的“历史真实”,然而,文献中有关过去的文字记载恰恰反映了一个群体对记忆的选择,这种被选择的记忆即是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群体依靠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失忆,参照当下的现实状况重构历史过去,以实现族群在社会中地位的重建,从而实现其现实利益。
邓州高山族八大姓氏所提供的家谱,都解释了其祖先的来源。邓州高山族家谱均有“台湾”“土著”等内容的记载。根据赵广军的考察,八部族谱都十分清楚地记忆着很确切的族群、番社名字。通过大量文献的梳理、考证, 可以从史籍中搜寻到与之相近或字异音近的台湾番社名字。
邓州高山族八姓七族对其族群来源一致性的记载便是其群体借用历史记忆创建族群边界的体现。从修谱时间来看,陈氏家谱修于同治六年(1867年),谢氏家谱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余六姓家谱均修于1941-1943年间。可以肯定的是,自上世纪40年代起,邓州高山族八氏有意识地利用历史记忆创造民族边界,通过族群共同的族源记忆凝聚群体认同,塑造该群体的边界与感情特质。
(二)口述中的历史记忆
口述中的历史记忆是历史记忆流传的另一种形式,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历史的内容与“历史真实”往往相去甚远,由于各种主观因素,有关某个群体的起源与流变的历史在口耳相传中难免出现讹传。但是,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口述历史的创造与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群体的自我认知。口述史不仅仅表现为本族内部对历史的记忆,也包括“他者”对某一群体的历史记忆,是从“他者”的身份对某一群体的认同。
有关邓州台湾村高山族的口述历史记忆,学者和学术机构都做了田野调查,大致可以反映出邓州高山族群体关于族群起源,族群认同等问题。河南省民族研究会会员涂征对邓州高山族群体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并从中获取了一定的口述历史信息。
据他发现,“台湾村”上营行政村的孩童在玩游戏中,因为输赢问题往往会向对方夸耀本家祖先。风俗方面,在葬礼仪式上,死者的直系亲属也会唱道“爹呀!尼牙呀!回去吧!你们放心回去吧!回到大海的彼岸,那里有日月潭,那里有阿里山,那里的香蕉菠萝赛蜜甜”。
可以看到,高山族老人及孩童,以及其他群体都对邓州高山族群体族源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其祖先来自台湾。这种历史记忆在当地人中间代代口耳相传,是其记忆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现实中的历史记忆
所谓现实中的历史记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过去生活中风俗习惯的延续和实践,它不同于以文字或语言等方式对历史过去的叙述和流传。邓州高山族群体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闽南化”“邓州化”,但是依然明显地保留了部分特有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是其群体历史记忆在现实中的体现。
“台湾村”高山族丧葬风俗中的“跳棺”与闽南地区的丧俗十分相近,但又有其特点。丧礼中,孝子要从棺材上跳来跳去,口中要念道“爹(妈)呀!回去吧!回到大洋(海峡)彼岸,那里有阿里山!那里有日月潭……”跳棺之后还要“送程”,即半夜子时,孝子及其组人要一起把棺材抬出家门,棺下放一木板,意为让死者漂洋过海。 三月初九的寒食节是邓州高山族一个特别的节日。据家谱记载,“周氏(迪摩达奥)父亲为山寨酋长,为了救出山寨的其他人,其父与全家八口自己站到柴堆上,葬身火海。迪摩达奥和他弟弟被家族长老藏到山洞里而获救”。
在饮食与称呼方面,邓州高山族并没有表现出特有的高山族特点,而是与闽营人所保留的闽南风俗十分相近,这也是高山族人长期与闽南人融合的结果。
三、“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所谓的族群认同,是一个族群利用客观存在或是虚拟的共同祖先和文化,有意识地实现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并由此实现这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群体进行“群体边界”的创建过程。历史记忆在“边界”创建中起到了“工具”的作用,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主要体现。存在于家谱记载、口述流传与现实实践的各种历史记忆,正是邓州高山族群体实现自我认同的工具,并由自我认同进一步实现族群重建。
(一)族群认同与族源记忆
邓州高山族家谱中的历史记忆与口述中的历史记忆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族源记忆。邓州高山族八氏来自台湾不同的部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八氏落户邓州后逐步实现同质化,形成一个有共同记忆的族群,并最终实现了族群的再造。这个过程中,关于族源的记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氏家谱中基本都记述了自己家族祖先的来源,除具体的部落名称外,均提到了“土番”“台湾”。在远离台湾的中原地带,共同的来源让来自不同部落的“土番”逐渐形成了群体的心里认同。邓州高山族的各种节日及风俗大多与族源有关,如寒食节对祖先的纪念,丧礼中对逝者归根的祈愿,等等。邓州高山族群体正是通过以族源历史为核心的历史记忆的流传和强化来创建族群“边界”,以达到族群认同。正是通过对族源的共同记忆,邓州高山族群体一步步塑造了该群体与周边闽南人及本地汉人群体的边界。
(二)族群认同与记忆再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开展以来,邓州高山族数量呈现出失控性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自称先祖系台湾土番基本上占闽营人、户数的10%;到2005年,高山族户、人比例分别达到了17.9%和20.1%。从数据上来看,邓州高山族的族群认同表现出了明显的高涨趋势,这种族群认同的高涨现象源于优惠的民族政策、民族的自我优越感等因素。本文讨论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希望探讨邓州高山族是如何通过历史记忆的再造实现其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
四、结语
通过以上文章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邓州高山族群体是如何通过其特有的历史记忆实现族群认同的,也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历史记忆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和流传的。邓州高山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一方面源于对祖先的追忆,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客观环境。能否在族群的认同与融合中实现群体的利益,成为一个群体是否进行族群认同的根本性因素。无论是初到邓州的高山族祖先选择与当地汉族通婚,还是上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中高山族数量的大量出现,都体现了这一点,历史记忆仅仅是一个族群进行族群认同的工具。这也解释了当下中国各地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民族村建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