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蔚然的戏剧艺术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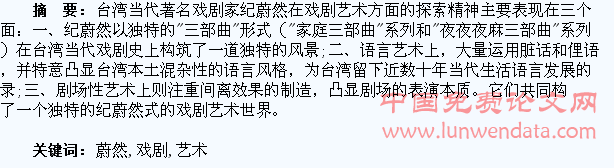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在台湾当代剧坛,纪蔚然是少有的坚持传统剧本创作的本土剧作家,从1978年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6部剧本,戏剧创作多集中于1996年至今,在台湾其剧作也是被搬演频率最高的一位。他的戏剧作品多与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充满着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2013年,纪蔚然获得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
纪蔚然在剧作中既有对于台湾当代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还有对于戏剧艺术本质的探索创新精神,它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戏剧类型的探索、语言艺术的探索和剧场性探索。在戏剧类型的探索上,纪蔚然以独特的“三部曲”形式(“家庭三部曲”系列和“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在台湾当代戏剧史上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语言艺术上,大量运用脏话和俚语,并特意凸显台湾本土混杂性的语言风格,即中英文夹杂,国台语夹杂,为台湾留下近数十年当代生活语言发展的记录;在剧场性艺术上注重间离效果的制造,通过戏中戏的情节编排、演员跳进跳出的表演形式和检场人的角色设计打破了舞台幻觉,凸显了剧场的表演本质。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纪蔚然式的戏剧艺术世界。
一、“三部曲”系列的创作和探索
至今纪蔚然共创作了两套三部曲系列,即“家庭三部曲”系列,包括《黑夜白贼》(1996)、《也无风也无雨》(1999)、《好久不见》(2004);“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包括《夜夜夜麻》(1997)《惊异派对》(2003)《倒数计时》(2007)。戏剧三部曲系列的创作不仅在台湾剧坛构成了“纪蔚然障碍”(1),而且呈现了解严后当代台湾人所特有的精神状态和焦虑处境。
“三部曲”一直是西方戏剧史上重要的戏剧类型,它往往具有辩证的主题、恢弘的结构和严谨的动作,且三部作品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纪蔚然的两套三部曲剧作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完整严谨的戏剧结构,它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两套三部曲剧作都是“以最小的关注点来影射最大的层面”[1]9,分别从家庭和个人层面呈现了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社会变迁,反映了台湾社会内在的精神危机与困境。
“家庭三部曲”系列藉由“家庭的崩解”反映台湾解严后时局失序的社会图景。较之于以家庭主题为主流的西方舞台,家庭主题在我国的舞台上仍是个开发不足的领域,而纪蔚然家庭三部曲的出现弥补了这一戏剧类型的不足,且对家庭主题的开发更为深入和系统。此外,《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好久不见》因聚焦于台湾本土家庭,其典型的地域特色和本土关怀特征也使其显得别具一格。
《黑夜白贼》的剧情围绕着林母心爱的首饰失窃为线索,通过案件推理与往事回顾交互行进,有如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揭开家庭的内幕,剧中凡是来过家中的所有亲人几乎都成了作案的嫌疑对象,而林母的儿女也不堪忍受家庭内部的谎言与伪饰,亟欲从中逃离出去,因此,在丢失珠宝的情节表象下,作者所要暴露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的感情与信任危机;《也无风也无雨》中的田家兄弟,只有在分配阿爸遗产时才难得聚在一起,却因遗产分配问题各执己见闹得不欢而散,家中的小弟田明文因对家庭内部矛盾不满,竟登报声明自己要和家人脱离关系、断绝往来,而他“真正想摆脱的不是家庭、不是血缘,而是那啃啮心灵的离散情绪”[2]6;《好久不见》则以碎片拼贴的戏剧结构呈现了在台湾家庭关系的变迁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块漂浮的碎片,他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毫无交集,甚至相见也不相识。虽然最后同一家族的亲戚们还是会为了争取房产开发的最大利益而共聚一堂,但这也只是表面形式的暂时复合。
从“家庭三部曲”的内容可以看出,剧中的家庭成员在各自的家庭中已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要么在家庭中备感压抑和窒息,如《黑夜白贼》中的林宏宽为此患上了精神焦虑症;要么意图和家庭断绝关系,如《也无风也无雨》中的明文,因此,家庭在这两部剧中只是徒具外表的完整,内在已崩裂瓦解,而到了《好久不见》则已彻底破裂为碎片。
纪蔚然在该系列中通过关于家的主题探讨,表达了对于家庭崩解的焦虑。这种独特的家的焦虑和台湾社会一直以来的家国并置有着莫大的关系。“回溯过往的百年,台湾人无论新来后到,‘家’的议题总是习惯性地放在‘国’的脉络下进行思考。没有‘国’哪有‘家’的意识形态,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也因此,台湾对于‘家’的危机意识,更深层地反映了人们对于‘台湾’的不安全感。而难以卸下的危机意识与不安全感,正是‘认同’的最大敌人。”[3]43因此,纪蔚然通过家的崩解其实隐喻了台湾社会内部的认同危机与自我分裂。它们在作品中也得到了形象的揭示:一是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形象的解构。例如《黑夜白贼》中的父亲已病入膏肓,失去行动能力,在舞台上从未现身;《也无风也无雨》中的父亲已失踪或死去,而其在子女记忆中的神话人格遭到颠覆性的扭转,原来是一个暴露狂;《好久不见》中的父亲则彻底缺席。从《黑夜白贼》的母亲“代父”,到《也无风也无雨》的“?s父”,到《好久不见》的“无父”,“去权威化”的父亲代表着解严后台湾政治威权的瓦解和堕落,也隐喻着凝聚并维系家国的集体共识与认同已丢失;二是剧中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缺失、互生罅隙隐喻着解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台湾政党和族群的自我分裂与内讧,它们共同在台湾社会中制造了离散和敌对的情绪,作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家庭自然也无法幸免于难。纪蔚然在谈到“家庭三部曲”的创作时,曾说过:“我家的转化和这个社会的变革几乎是亦步亦趋的。”[1]9因此,通过“家庭三部曲”记录台湾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既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是该系列剧在台湾剧坛深获好评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家庭三部曲”系列是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向外审视时代社会的变迁,那么“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则主要通过知识分子向内的自我反省来表达对于台湾社会发展的内在隐忧。该系列主要以昔日同窗好友的聚会作为戏剧情境,以知识分子和男性群体为主人公,以小窥大地呈现了在台湾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世代所特有的存在精神状态。《夜夜夜麻》、《惊异派对》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幻灭以及在现实中的怯懦与沉沦。两剧中的人物都经历过理想燃烧的1980年代。《夜夜夜麻》中的主人公们大学时期都曾是热血的文艺青年,如今他们相聚打麻将,却只能在相同的回忆中感伤,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中愤怒;《惊异派对》的主人公们也参加过“学运”,但是在现实的威胁和诱惑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妥协和放弃,这不仅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遗憾,也导致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幻灭与沉沦。《夜夜夜麻》中的知识分子在夜夜的麻将声中选择了自我麻木;《惊异派对》中的主人公们也只剩下了精英式的喟叹和无奈的幻灭,正如小马所说:“我们当初所支持的人,搞了半天跟我们后来推翻的人没什么两样。改革、改革,我们到底改革了什么?当初我们那一票一起奋斗的同志,没错,是混得很好……但是,我想问这些人:我们憧憬的美丽新世界跑到哪去了?”[4]130与《夜》、《惊》中的知识分子还有自我反思的能力相比,《倒数计时》中21世纪的青年一代则已对社会毫无理想和憧憬可言,他们对自我以外的世界持冷漠疏离的态度,就像剧中人物杰瑞对上一代人大牛所说的:“我可没有你们这一代的幻灭感。从来就没有憧憬,哪来的幻灭。”但是一心赚钱的他们仍对台湾的现实不满,因为“整个环境让人分心,把心思浪费在没有正确答案的事情上”[5]21。在发泄了对台湾内部政治环境的不满之余,剧中的年轻一代选择了远离政治,以游戏的姿态面对人生。
从怀抱激情到幻灭再到放弃,“夜夜夜麻三部曲”通过对中青年人物群体精神状态的书写呈现了台湾不同世代的焦虑,它不仅触碰了两个世代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犹疑的痛苦,并且从他们那愤世嫉俗和沉沦的言行中看到了人物对于自己和社会的不满、对过去的失落、对未来感觉不安的情绪,并揭示出当前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改变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与幻灭感,或许只有在“夜夜夜麻”完结篇《倒数计时》中,剧中人物张飞和山猪身上所存有的真情和行动力才是未来的救赎希望所在。
在“家庭”系列和“夜夜夜麻”系列作品中,以小窥大的视角和严肃的社会关怀不仅使两套三部曲在主题内容上自成一体,而且在三部曲这种具有更大篇幅和时间跨度的戏剧形式内,主题内容也得到了辩证的发展和统一。
其次,两套三部曲系列结构严谨,戏剧焦点凝聚,格局虽小却活力十足。从戏剧情境来看,两者都属于传统的客厅剧系列,因为剧中情节动作的发展大都是在客厅内完成,且多数剧作时间与场景高度集中,情节单一,具有三一律的创作特征。以“家庭三部曲”为例,《黑夜白贼》是典型的三一律剧,虽然《也无风也无雨》中的两幕之间有时间间隔,但是相对来说,每一幕仍遵循了三一律原则,《好久不见》戏剧场景多变,采用了拼贴结构,情节发生在一天之内。“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中,《夜夜夜麻》、《惊异派对》和《倒数计时》则时间场景固定集中,都具有三一律的创作特征,因此两套三部曲系列的戏剧作品都具有集中整饬的美学特征和较强的戏剧张力。
再者通过人物再现手法连贯三部曲,使三部曲之间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虽然“家庭三部曲”各自在三个不同的家庭内展开剧情,“夜夜夜麻三部曲”也是以三个不同的人物群体作为表现对象,但是通过人物的再现和串联,使三部曲之间形成了互相映照和联系的整体结构,而这些再现的人物形象多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意味。例如“家庭三部曲”中的清水,其名字与剧中充满勾心斗角之污浊之气的家庭内部成员形成了反讽和对比的关系,加之清水的身份是海员和水手,代表着反世俗的精神和浪漫情怀;“夜夜夜麻三部曲”中的山猪,无论是其本土化色彩浓厚的名字还是其底层的身份、直来直去的性格行为,都与剧中其他使用英文名字、拥有上流社会身份、外表斯文的人物形成了对比。山猪象征着当前台湾社会中所缺失的真情与行动力,而它们才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除了三部曲系列,人物再现法还出现在其他的剧作中,如《嬉戏》和《疯狂年代》中的阿浩与小歪的重复出现。这种人物再现法的使用使纪蔚然的剧作更具整体感和个人特色。
从以上两套三部曲的创作来看,纪蔚然较为成功地做到了把三部曲这种外来戏剧类型或形式进行本土化的尝试和改造,描摹了解严后台湾当代社会中人们存在的精神图像,成为台湾戏剧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此外,像侦探和推理这些原本属于西方戏剧的元素也为纪蔚然所用,如《黑夜白贼》采用推理剧形式,《影痴谋杀》则是一部侦探推理剧等,这都体现了纪蔚然在戏剧类型方面积极开拓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二、语言艺术的探索
纪蔚然说他戏剧的特点是希望在语言上有所突破,因此他还是一个偏于传统的注重语言对白的剧作家,为了更好地发挥话剧以语言对白为主的艺术特征,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他在《夜夜夜麻》一书附录的“作者的话”中说:“所有剧场元素当中,语言是我着力最多的实验。我摸索节奏,大量运用脏话,玩弄成语、滥调、俚语、黑话。我希望跳脱文艺腔的窠臼,避免西式语法的难堪,杜防日常说话的琐碎,进而发展出一种既生活且风格、既很口语又带有诗意的对白。”结合其剧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纪蔚然戏剧中的语言艺术探索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量使用脏话和废话的语言特点。在纪蔚然的剧作里,脏话的使用量和频率都是极高的。通过对脏话的使用,纪蔚然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所具有的表达情绪、增进情谊以及针锋相对的独特功能,并揭示了在人们使用脏话的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危机与困境。以《夜夜夜麻》为例,四位男主角的对白就充满了脏话和语言暴力,不仅“干”声连连,“他妈的”不断,还有“操”、“Fuck ”、“Shit”、“我靠”等词语散落于对白中。如剧中一段打牌过程中,Peter起身接电话的片段: Peter:忘了。(讲电话)喂?干嘛?(许久不讲话)你等一下。(对其他三人)你们等一下。
(Peter走向舞台左边,由左翼幕下)
诗人:操!
马克:他妈的!
山猪:Fuck ![6]31
剧中的Peter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的家庭生活名存实亡;马克是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却也难以压抑猥亵的内在;诗人才华洋溢,却在绝望中走向自我放弃的道路,这些原本应保持彬彬有礼的社会形象的角色在粗鄙卑贱的脏话使用过程中暴露了其内在的不堪与堕落,他们只能坐在那里,通过脏话发泄对现实和自身的不满,逞口舌之快,却丧失了行动的意志和能力,脏话对于他们而言更多暴露了其充满绝望和无助的精神困境。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口头的脏话越是严重,说脏话的人意图对抗社会环境的冲动越是强烈。在纪蔚然的剧作中,也可以看到由于当代台湾人非常不满意岛内政治社会现状,使他们往往在使用脏话的过程中反而能取得顺畅的交流和沟通效果。例如《无可奉告》“场景七”中的出租车司机与乘客原本互相提防,冷漠相对,没有交流和沟通的欲望,但是在发泄对台湾社会和交通的不满方面,通过说脏话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找到共同的话题:
“司机突然紧急刹车,乘客身子往前急倾。
司机:他妈的,开车不长眼睛。
乘客:就是嘛。
司机:台湾交通这么乱,就是因为有这种杂碎在开车。
乘客:一点都没错。妈的,有一次,我……
乘客以下只比手画脚,边讲边往右边的座椅靠。”[5]179
还有该剧的“场景一”中,自由人、上班族、研究生都在等待雨颜, 因雨颜的迟到,三人把各自的愤怒和不满都迁移到他身上,并准备不顾情面地声讨和质问雨颜,而当雨颜真的来了之后:
“雨颜:他妈的,台湾完蛋了!
三人同时反应:‘怎么啦?’‘啊?’‘什么?’
雨颜:我刚才骑车到捷运站,结果……
雨颜只是比手画脚,其他三人不时发生反应:‘啊!’‘真的啊?’‘哇铐!’‘有这种事?’”[5]144
众人原本对雨颜的迁怒因转移到了对台湾现状不满的发泄得到消解,而脏话所体现的这种增进情谊的功能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微妙反讽。
除了脏话,纪蔚然还在《好久不见》、《无可奉告》中大量使用废话,揭示现代人内在的精神空虚和存活的焦虑。废话包括各种广告用语和“打屁语言”的滥用。《好久不见》中的小维在和朋友阿敏交流时所使用的多是广告用语,“还好有新的多芬。新的多芬的滋润效果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大象皮的地方不见了。我好想遇见我以前那个同学,因为现在正面、反面,都很好看。”[2]224剧中只会复制广告用语的小维已彻底异化为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无可奉告》则是对于台湾流行的“打屁语言”的真实记录。所谓“打屁语言”就是指用来消磨时间、消遣彼此的连篇废话。在片段5“所以我们怪罪吴宗宪”中指出,虽然我们怪罪吴宗宪“那种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语言,那种纯属打屁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是他的亲身父母,……他是你我的缩影。”[5]168片段6“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跟别人打手机”,一对男女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话,过了数秒,女朋友接了个电话:
“喂?……刚起来啊?一副声音还没化妆的样子……还有谁?除了他还有谁……我喝latte ,他喝espresso……明天?还没有决定……等一下?也还没决定。等我们确定了再打给你。好,拜。”
男朋友接下来也接了个电话:
男朋友:“喂?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还不一定……如果没地方去我们等一下就过去。好,拜。”
在两人都结束手机通话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女朋友:亲爱的。
男朋友:什么?
女朋友: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跟别人打手机。
男朋友:亲爱的,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不想一个人打手枪。[5]176
由以上对话可以看出,这对情侣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都更愿意选择与不在身边的朋友们寒暄客套,说些无意义的废话,以向朋友证明自己并不孤独和空虚。在两人看似热络的交际外表下,其目的是为了让外表的喧哗掩饰内在的空虚以及不知道将要做什么的焦虑。因此,这种打屁的语言:“它有填补的作用,让我们暂且忘却生命的缺口。更重要的,它提供了一个出口,让我们从言谈中纾解那种幸存苟活的焦虑。是的,日子无奈到,存活的焦虑已逐渐取代了存在的焦虑。”[5]125在大量繁殖和堆砌的废话背后恰恰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对于内在灵魂追求的空洞和苍白,因此无论是脏话和废话,都只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伪装,它们都掩盖不了现代人内在所经历的精神危机。
二是凸显台湾本土多元混杂性的语言风格。中英文、国台语夹杂的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台湾人文化认同的多元化与混杂性。“解严以来,台湾的语言真的变了,而语言的转向直接反映了某种程度的文化革命。……面对目前杂交混种的语言,诸多忧心之士已相继提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警讯,大com其plain。但,换个角度来看,今天无厘头的语言未尝不是对昨日八股语言的反动。”[5]122
“家庭三部曲”系列之《也无风也无雨》刻意呈现国台语夹杂的情形,藉以反映台湾的语言生态。它虽然描绘一个‘台湾人家’,但为了反映剧中人物的年龄背景及意识形态,我很小心地为每位角色设定他的语言基调。虽然各有基调,每个角色会视情况和说话的对象而随时换挡变调,甚至在一句话里都会出现语言杂交的情况。如此的选择原因有二:国台语交杂的对白较贴近生活、较写实,此其一;台湾已不再是某种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反而是各种语言杂交的现象,此其二。”[1]11剧中的清水大量使用闽南语的俗语和谚语就是典型的例证,诸如“桩脚”、“歹势”、“麻吉”、“尾牙”、“代志是这样的”这些台语中的词汇和句法大量出现。“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还大量呈现中英文夹杂的情形,尤其是《倒数计时》,通过这种语言对白反映了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一代在语言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亲美情结。 语言作为种族认同的特征,其背后也往往蕴含着一定的认同诉求。而纪蔚然的戏剧语言创作观就体现了其反对纯粹主义的认同立场,他在2012年《1970那年我十六岁》的杂文中写道,就在那一年“我的认同意识出现了裂隙。不过裂隙并不代表危机,它对我而言不啻是至今引领着我的启示,当时我已隐约体悟,认同不需要纯粹,亦不应是单一选项。”[7]这种态度和立场反映了作者力图通过混杂性的戏剧语言呈现来传达一种更为理性和包容性的认同诉求。
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纪蔚然戏剧语言的腔调比较生动、贴切,而他出版的剧本所使用的也是带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话,不是标准的台湾国语,比较俚俗的字眼也都有国语的注解,虽然读者阅读剧本时不会遭遇困难,但演出时却有些受限,这也是纪蔚然的戏剧为什么会在台湾本土深受欢迎,而在内地上演却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所在。
三是植入时代流行用语以针砭时代社会的弊病,制造讽刺幽默效果。纪蔚然敏锐地捕捉到台湾当代的流行语言,并在作品中予以呈现,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时代文化隐忧。例如纪蔚然在剧作中呈现了当代台湾日常语言“可爱化”的现象。以《惊异派对》中的两个大男人小马与大牛讨论某家餐厅时的一段对话为例:
“小马:去过,还不错,但是他们的炸虾千万不要碰。
大牛:为什么?
小马:虾很小,粉太多。
大牛:粉小气的意思!
小马:粉粉小气。”[4]125
在台湾,“粉”小气就是“很”小气的意思。这种构词来源于电视媒体中艺人表演的口头禅,由于它给人新奇可爱的感受,一度在台湾流行开来。类似的语言表达方式还体现在《乌托邦Ltd》中的新时代人物形象Virus身上,她在面对他人的吩咐与指责时,总是以一句充满可爱表情的“O喔”带过,以逃避或转移自身可能面对的难题。纪蔚然通过这种“可爱化”的用语使用,不仅证明了“台湾的语言从以前的老成持重演变至今天的年少轻狂。过去,小孩讲话故做大人沉稳状;现在,大人讲话故做小孩可爱样。过去的语言取其不可承受的重,现在的语言取其不可承受的轻。”[5]124更揭示了在媒体凌驾一切的年代里,受流行文化的影响,人们在语言交流上日益逃避意义的沉重感,改以更具轻巧和娱乐性的话语方式进行沟通,而作为思维和文化产物的语言,它的可爱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表达逐渐由深刻转向轻盈肤浅的发展趋势,因此,纪蔚然在杂文《向可爱宣战》中写道,“可爱是台湾公民走向成熟的最大阻碍。可爱让我们长不大,我们生活在可爱的深渊里。”[8]
除了语言的可爱化现象,纪蔚然还把台湾政坛上使用过的引人注目的粗鄙语言植入剧作中以暴露台湾“民主”政治堕落与恶化的品质。如《倒数计时》中的大牛在对白中曾五次提到了“LP”(2),讽刺了台湾政客的粗俗嘴脸;《拉提琴》中植入了邱毅和陈致中电视台人身攻击和谩骂的语言片段。两位政治人物之间并没有严肃深刻的政治哲学观点交锋,只有谩骂式的人身攻击,邱毅不断提及陈致中“开查某(嫖妓)”,陈致中则频频追问邱毅的身份证和护照上的相片有没有戴假发,俨然一场恶俗的博取公众眼球的政治闹剧表演,折射出台湾政坛政治道德沦丧,核心价值观丢失。
纪蔚然通过对台湾当代语言变革的敏锐观察,在剧作中呈现了独特的语言现象,强调语言所承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甚至从语言微妙处透视文化的变革。这都赋予了他的剧作以一种生动亲切的时代面貌,与一些重看不重听的舞台剧相比,语言在他的戏剧中夺回了中心的地位,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剧场性探索
剧场性是戏剧的本质属性,它是指观演双方共享同一时空的现场性,具有打破故事虚拟时空的幻觉性,从而使观众以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个性经验进行审美、思辨和氛围体验等特征。在这方面,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剧场性艺术追求。虽然纪蔚然的作品都是由他人导演,自己不具有导演身份,但他也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剧场性意识的剧作家。纪蔚然1990年代的剧作多采用传统的偏写实手法,如《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夜夜夜麻》等,进入21世纪以来,他开始尝试和利用更多的剧场性手法来打破舞台幻觉,制造间离性效果,其剧场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整体的“戏中戏”结构设置。戏中戏作为典型的剧场性艺术手法经常被当代剧作家们普遍采用,纪蔚然使用这种剧场性手法的作品有《一张床四人睡》、《嬉戏Who-Ga-Sha-Ga》和《疯狂年代》,在这三部戏剧作品中,都是由演员的演戏和排戏过程作为主要情节,导演和演员们既在舞台上排戏,又在戏外发展各自不同的故事,因此现实与幻觉、故事与表演等多层次的结构成为了全剧的核心。例如《一张床四人睡》中的四个人物即两对夫妻之间在排戏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各自的情感危机,他们在戏里戏外寻找各自的精神救赎;《嬉戏Who-Ga-Sha-Ga》中的演员小歪和剧团导演阿浩为了从已成为废墟的台北城中逃出去,临时编排各种戏剧片段以应付岗哨检查,通过他们的演出嘲讽了台湾极度庸俗和肤浅化的媒体文化;《疯狂年代》同样是阿浩带领演员为了挽救剧团生存危机而排演一部既能代表台湾精神又能反映全球化特征的戏剧作品,讽刺台湾社会的全面综艺化。
其次是通过局部的角色设计制造间离效果。纪蔚然有时让演员在适当的时机跳出角色,以演员的身份发表对戏剧本身的评论,如《倒数计时》的舞台指示,
“此时灯光变化,客厅明亮了起来,只见小恬和波罗回复到‘演员’的身段,讲话的神态与他们饰演的人物大相径庭。
小恬:这出戏还走得下去吗?
波罗:我也在怀疑。
小恬:从我们两个上场,对白就开始言不及义。
波罗:变得没有重量,轻飘飘的。
小恬:编剧严重歧视我们年轻人。
波罗:对嘛,我们哪有那么肤浅。
小恬:对嘛。”[5]55
有时还灵活发挥检场人这一角色的功能。例如在《无可奉告》不仅有检场人上下场搬移舞台道具,还给他们设计了台词,让他们更换完道具后坐在观众席中,自然地完成了表演场景与后台场景的切换;《拉提琴》中则安排了三位默剧演员,他们与正戏的关系随情境而变:时而烘托、强化,时而嘲弄、疏离。有时,他们只是道具或检场。此外,纪蔚然还让自己在作品中现身,如《嬉戏Who-Ga-Sha-Ga》中就有“纪蔚然”这一编剧的角色,而他在杂文中经常自称为冷伯,其剧中人物对白也经常提到“冷伯我”,如《夜夜夜麻》中的山猪,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纪蔚然自身形象的投射,它们既是一种疏离手法,也构成了纪蔚然戏剧的独特标签。 纪蔚然之所以选择在剧场中使用多种间离手法与其对当代叙述环境和布莱希特的认识有关,“当代叙述很难不裂隙百出,只因说话的人不再相信自己的故事,阅听大众也不再相信听到的故事。这般情境在媒体凌驾一切、网路浸透所有的年代只怕会愈趋严重。如此一来,说故事的原始意义――即建构意义――若未荡然无存,也已大打了折扣。裂隙看似不幸,但它可以促使人们反思说故事这档事。”[9]134因此,纪蔚然根据叙述的时代演变特征故意暴露和制造这种戏剧文本中的叙事裂隙,他的《拉提琴》剧中原有副标题“向布莱希特致敬”,后来为了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忍痛舍去这个副题,但布莱希特仍是纪蔚然的戏剧乡愁,他说,“资本主义淹没一切的世纪,我们更需要布莱希特这种剧场艺术家。戏剧史上一边讲故事一边拉提琴的,他是第一位。他的史诗格局,他的辩证精神,他的疏离主义,他的艺术宏观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后人无法如实复制,但起码可以再现。”[9]135可见,纪蔚然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运用表演及其他元素营造疏离辩证的效果也是其对于布莱希特史诗剧场艺术的一种学习和再现。
由于纪蔚然主要是一个编剧家而非导演,这影响了他在演出排练和舞台实践方面对于剧场性探索做出更大的突破和创新,因此与戏剧类型和语言艺术的探索相比,纪蔚然在剧场性的探索方面还是显得稍逊一筹。
总的来说,纪蔚然在戏剧艺术方面的探索因具有强烈的本土关怀和批判精神,如关注台湾本土的时代社会变迁和家庭生活、使用台湾本土化的语言对白等,顺应了当代台湾在文化艺术方面追求本土化表达的诉求,而其对台湾政治社会文化的讽刺批判与鲜明的人文精神关怀又使其剧作具有了较高的思想价值,两者共同造就了纪蔚然戏剧在台湾当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注释:
(1)该名词来源于江世芳2004年11月在台北《PAR表演艺术》第143期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名字。
(2)这词是2004年台湾“外交部长”陈唐山用台语说出来的,原话为“新加坡在捧大陆的卵泡”,就是说新加坡在拍大陆的马屁。卵泡,即男人的阴囊。记者播新闻时,不好说出口,就说成LP了,后来LP就成了台湾家喻户晓的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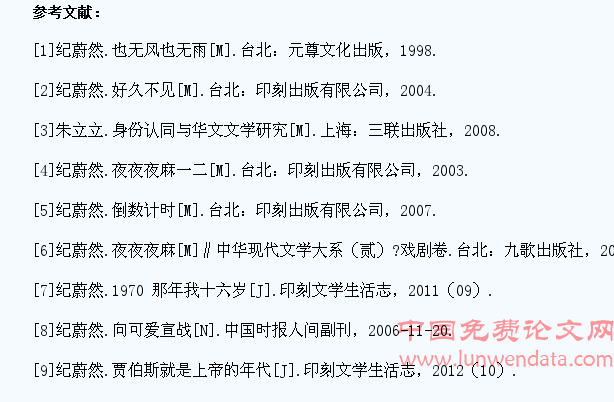
- 上一篇:论当代艺术对消费符号的挪用:模拟
- 下一篇:高效课堂提问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