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抑之智:论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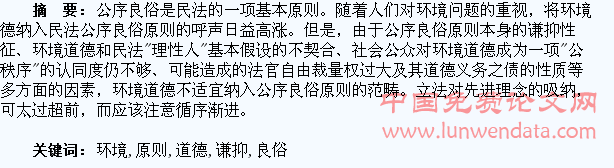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82?09
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的规范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其统领着民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另一方面,其相对于具体制度而言,具有抽象的特点,因而能较为灵活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有学者指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基本的法律都有很长的寿命,立法者必须考虑到将行之久远的法律对他们所不能预料到的情况将如何处理,因而设定像基本原则这样稀疏的有意义形式,向有权机关提供广阔的解释空间,以使其通过解释的形式补充和发展法律”。[1]具体到民法领域,民法基本原则便蕴含了民法规范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不能为现有的规范、制度所涵盖的权利现象进行调整的弹性空间。因此,我们应该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具有类似“空筐”的基本结构,既保证了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不会超出立法时预设的外延、从而使其“扩张”不至于任意化,又能最大限度为解释者提供弹性空间。
对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方面,学者们的论述存在一定差别。①在民法典草案起草过程中形成的几个版本的建议稿中,对民法基本原则组成的表述也不尽一致。②但笔者注意到,无论何种表述形式,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拥有广泛共识的。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种,公序良俗原则也存在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其外延的可能性。学者一般认为,公序良俗具有引致功能,即将法律外的规则引入法律内,使本不具有法律效果的一般道德规范具备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效力评价功能和违法性构成功能。“公序良俗犹如一根虹管,使民法得以不断吸取法律外的社会中的营养,不致与发展的社会脱节太远,从而可以永葆青春”。[2](169?170)当前,便有将“环境道德”(或者表述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的呼声。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有关公序良俗原则的解释中,基本不包含可持续发展这一环境道德、生态伦理的内容,这是由当时所处工业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局限所决定的。但在当前社会,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入,对“环境道德”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考虑到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民法公序良俗条款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并呈日益高涨之势。
(一) 环境道德的勃兴
有学者认为,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三重转变”,即: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世界经济形式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3]笔者注意到,这“三重转变”都包含着重视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环境道德”的提法出现了。
应该说,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继续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我国也是如此。我们可喜地看到,至少在官方层面和知识分子层面,③对环境道德的重视度是有很大提高的。但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之中呢?笔者在下文将会详细分析。在这之前,首先简要介绍有关学者的主张。
(二) 来自民法学界的呼声
民法学界先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较少,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上文谈到的,这是由过去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够所决定的;二是因为我国民法学界在近三十年来担负着新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从无到有”的历史重任,有太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研究,而这个问题似有“后现代”之嫌;三是我国民法学者注重对国外“法制文明”(尤其是各国立法)的引介,法、德等国制定民法典时根本不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④因此,我国学者对之缺乏关注,便不难理解。然而,新世纪以来,围绕民法典制定产生的学者建议稿,改变了民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缺乏关注的状况。
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其在题目中便彰显了“绿色”二字,从其规定的有关条款看,对于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力度是比较大的。正如其谈到的,该草案“除了理想型的特征外,还具有‘绿色’的特征和人文主义的特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当作基本原则和所有权的义务规定,并在一切其他规定中体现这一原则”。[4]具体到民法基本原则方面,徐国栋教授在草案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指“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其他动物之权利的原则”。[4]虽然徐教授的“制度安排”中将绿色原则作为与公序良俗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我们仍可以得出,徐教授设计的制度安排中,公序良俗原则是应该包括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这是因为:如其在上引“对‘立法’目的阐释”中所言,环境保护是“在一切其他规定中体现”的原则,且如后文将会分析到的,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一般不会直接在法律条文中明定、而多通过司法机关确定。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徐教授是主张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之中的。
应当注意到,《绿色民法典草案》问世后,民法学界确实围绕此展开了论战,但主要争点集中在所谓“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之争上,对民法是否需要“绿化”的问题,则少有涉及。事实上,徐教授对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为何要“绿”、怎么个“绿”法,是有颇多论述的,而且其认为这个草案“最有思想性”,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贯穿始终的“绿色原则”。[5]笔者认为,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争论相对较少,似乎有些遗憾。 不过,《绿色民法典草案》的问世,终究意味着,是否需要在公序良俗原则中,包含环境道德的有关内容,成为民法学界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 来自环境法学界的呼声
在这个问题上,与相对冷清的民法学界相比,环境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则要热闹许多。吕忠梅教授在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从民法视角审视环境问题,后来又创立“环境民法学”的研究方向,具有开创性贡献,其观点颇具有代表性。
吕忠梅教授首先肯认了民法基本原则应具有开放性的观点,认为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公序良俗以新的含义,公序良俗原则也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处理着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已形成剧烈冲突的现实条件下,理应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6](104?105)应该说,这一认识在环境法学者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二、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界定
欲分析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首先需要对该原则的内涵、外延作一比较清晰的界定。然后,才能据此分析环境道德与该原则是否具有适配性。
民法是私法,是任意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这一自由并非毫无限制,公序良俗原则便是法律对契约自由的直接限制。在我国语境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分别指代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内涵与外延存在区别。[7]但在国外民法和民法学上,对这一问题主要持“两者统一”的观点。⑤诚如学者所言,“从根本上讲,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概念并无本质的不同”,“善良风俗是公共秩序的特殊组成部分”。[8](195)基于本文讨论主题,笔者不对两者的“分合”问题作探讨,仅从形式上将两者区分开来,分而论之。
(一) 善良风俗的主要内容
善良风俗与一国的最具根本性的道德习俗紧密联系,因此在不同国家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道德(尤其是根本性的道德准则)方面的趋同性比较明显。而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性条款,其抽象性、统领性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在立法中明确阐释应具备的基本内容,而只能留待司法实践通过判例的形式加以确立。
一般认为,善良风俗原则适用于违反性道德的合同、赌博合同、为获取其他不道德利益而订立的合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合同、违反一般人类道德的合同。[8](196?199)也有学者将反人伦、违反正义观念(如劝诱犯罪的契约)、极度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营业自由、处分作为生存基础的财产、显著射幸者等作为典型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9]
我国社会对“道德”“风俗”等问题的认识,一向存在较大(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这是由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及由前两者导致的认知差异)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这就让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更加不愿意援用该原则。从我国法院的司法判例看,少有直接援引此原则者,曾热闹一时的“泸州二奶遗赠纠纷案”,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曾引起全社会巨大反响(尤其以负面反响为多),而这也给法院适用“善良风俗”原则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二) 公共秩序的分类和主要内容
公共秩序的一种重要分类是政治公共秩序与经济公共秩序的分类。前者被认为是“原本意义上的”公共秩序,是为了保护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保护国家、家庭和社会秩序);后者则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若干强制性规范对当事人间的财产交换直接干预,关注双方当事人间交换关系的平等。[10](172?173)
从特征上言之,政治公共秩序立足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某些“永恒”原则,从而具有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点;与之相对,经济公共秩序的政策性特征比较突出,其具体内容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创新性。[8](210?211)
这种公共秩序的分类,源于法国民法的理论,由于对我们下文的分析很有作用,所以在这里笔者引介过来,一来作为后文分析的铺垫,二来也埋下“伏笔”。
(三) 环境道德的“对号入座”
分析了公序良俗原则的构造之后,我们便需要思考:假设环境道德原则被纳入公序良俗原则之中(这个前提假设很重要),其应属于该项原则的哪个部分呢?笔者认为,根据环境道德的性质,其应该归入“公共秩序”的范畴,更进一步地,应属于“政治公共秩序”。
首先,环境道德不是一种“善良风俗”,至多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秩序”。也许,环境道德成其为一种“道德”,但这并不能保证其进入“善良风俗”的范畴。从善良风俗的内涵看,并非所有的道德都应进入这个范围,仅有根本性的、与人类本性有关的道德要求,才属于“善良风俗”。易言之,善良风俗涉及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如自杀契约之无效、限制人身自由合同不可取,大抵如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国对“善良风俗”的范围,普遍采取的是一种“逐渐限缩”(至少是保持稳定、不扩张)的态度,如违反性道德是否属于“善良风俗”调整范围,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具有社会共识了。而公共秩序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的某种利益,其外延具备一定的可扩张性。这些特征都使环境道德进入公共秩序,至少具备了技术上、形式上的可能性。而且,环境道德本身可以理解为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大和谐”,也可以从“秩序”的角度理解这种关系。而另一方面,“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之类,更类似一种尚未为所有人接受的“理念”“思想”,且其并非直接源自人性(若依人性,恐怕掠夺式开发、“与天斗其乐无穷”更符合人类本来的认知),将其视作“善良风俗”之一种恐怕不妥。因此,笔者认为,相对善良风俗,环境道德更适宜纳入公共秩序范畴。
其次,在公共秩序的二元结构中,笔者认为,环境道德形式上属于政治公共秩序之一种。这比较容易理解:经济公共秩序主要是国家通过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间财产交换关系的直接干预,目的乃是平衡双方利益、避免过度的不公正,进而从这个角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显然,环境道德,并不直接涉及双方当事人间的“不公正”,其立意是避免“人与自然间的不公正”。环境道德的基本要求,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成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违反这些要求,可以视为损害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笔者认为,环境道德更适宜纳入政治公共秩序范畴。 最后,需要强调,上面讨论的环境道德“适宜纳入公序良俗中的何种部分”,是建立在“环境道德应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假设之上。下面,笔者便会论证,这种前提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而之所以仍要作上述探讨,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对号入座”,是下文分析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前提和基础。
三、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原则的适配性考量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只能说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决定环境道德必须进入公序良俗原则的涵盖范围。要给环境道德“正名”,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适配性考量。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环境道德并未通过这些考量。
(一) 人性基础考量:“理性人”的现实和“生态理性经济人”的远景
“理性人”的现实和“生态理性经济人”的远景之间的距离,何止千万里!民法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它并不苛求民事行为主体“强健”“智慧”,只要求其具备基本的行为能力和理性预期。因此,民法的人性基础是“理性人”假设,民法也被称为“中人之法”(而非“精明人之法”)。这里假设的“理性人”,在行为中主要遵守一定的经济原则、效益原则,更注重考察的是个人的利益⑥。此种情况下,让他们认识到“要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为自身着想、还要虑及子孙后代利益(所谓‘代际公平’)”,似乎有要求过高之嫌,此时的人性假设早已超出“理性人”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高于“理性人”的人性假设。⑦这些假设的基本共同点是,在传统理性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衡量基础上,增加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意识(有些理论甚至主张用“生态人”完全取代“理性人”假设)。但笔者认为,人性的假设,虽然仅是一种“假设”,但只有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才有实际的意义,否则,过于理想主义的人性假设,无论理论上如何自洽与完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无所裨益的。就现阶段的人性基础看,“理性”假设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若是另立“生态人”等人性假设,将冲淡民法“理性人”假设的色彩(因为两者间在某些方面尚存在矛盾之处,虽然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克服)。而如果淡化、甚至否定“理性人”的假设,等于否定利益动机,人们将甚至不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如何进行选择和交易、生产、消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复存在,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沦为空谈,[6](142)须知道,“可持续发展”之核心,乃是“发展”,而非其他。更何况,从人性之本质看,我们必须承认,“自利”乃是“人皆有之”,这无关道德评判;要让人们舍利己之行为不为,去保护生态环境,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君子,恐尚且不为也!况庶人乎?
也有学者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在沟通与协调的理念指引下,提出了“生态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标准。[6](145)其基本理论框架是:将“生态理性”纳入“经济人”(即笔者所用“理性人”之表述,下同)的理性之中,既可以保持“经济人”在一般经济性活动中的正常利益,同时又增加生态性的考虑,以实现对“经济人”的生态性规限。该标准是一种既高于传统民法“理性人”标准,又没有脱离“理性人”之“逐利”等基本属性,是“将人的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共同考虑、将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协调的新型人性标准”。[6](145?146)
笔者认为,这种人性假设的基本要义便是:将对生态环境的考量纳入理性人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之中。易言之,行为主体在为一定民事行为时,在考量其行为后果是否“经济”“有效率”时,理性的分析标准除了现在的“利益”标准外,还包括“生态环境”标准。应该说,这在理论上是较有合理性的。但是,所谓“知易行难”,民事主体即便能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这种认识往往是抽象的,即他们往往并不认为环境对自身有直接相关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恐怕较少会真正分析“环境效益”“生态标准”。要实现该学者的目的,涉及到人类认识层面的重大变化,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更需要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内心深处的“共鸣”,岂能简单地从理论上“做加法”?简言之,“生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仍然不符合当前的基本人性状况。即便这种人性状况是可以达到的,恐怕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且要付出相当艰巨的努力。法律的保守性,决定其只是彰显和反映一定的社会观念,其(往往)并不能担当社会变更的重任。
(二) 调整对象考量:追求面面俱到,只恐面面 不到
正如本文已经(并将继续)强调的,环境道德在现代社会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这不代表应该通过民法来规定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制度之间的适配性。于是,我们有必要考察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包括环境道德?
有学者将民法区分为商品社会的民法和现代化、绿色的民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民法始终是那个民法,一个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具有以人为本色彩的部门法。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每一部民法都是一部“人权宣言”,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并不存在所谓新、旧民法之分。而世间所有事物皆不完美,民法也有其固有缺陷。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对弱者权益的损害这一类的问题出现,更是表现出传统民法制度某种程度上的“不完美”。但这仅仅是要求我们呼应时势变化,革新整个法律体系,而非要求我们在民法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调整商品流转关系时(几乎)无往不利的民法,若是用来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力有不逮。事实上,法律体系为回应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已经作出了革新――环境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吗?我们相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专门法律调整方式,要比在民法规范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更加有成效。民法规范,还是应集中自己规范的着力点,干好自己的“本行”――调整财产和身份关系,追求面面俱到,很可能导致面面不到的后果。
有学者也曾进一步论述,认为民法调整“绿色问题”(如所谓资源、环境问题),其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认为民法的调整对象中暗含了绿色问题,认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解决的其实就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问题。其将民事主体解读为“欲望主体”,将民事客体解读为“欲望对象”,从而认为民法“负责处理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该学者举《十二表法》中的“绿色规定”作为民法一向调整生态关系的例证。⑧笔者认为,这种分析的“理论推演”色彩过浓,仍未很好回答:为什么一定要由民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而其所举《十二表法》的规定,并不能证明民法应该调整生态关系,而是由于古代法律制度发展不成熟,多少带有“诸法合体”色彩,试问,谁说《十二表法》就完全是民法规范呢?即便假定《十二表法》的有关规定确实是民法规范,但在现代社会,法律部门划分愈益精细,由新产生的法律部门调整环境、生态问题,更加有效,而这恰恰是制定《十二表法》的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法制条件。以古喻今,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并不合适。 综上所述,从民法调整对象角度看,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规范(尤其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中,可能导致民法调整对象的混乱,最终不利于民法的有效施行。
(三) 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考量:谦抑原则
民法的精神内核是“权利宣言”,它是赋予民事主体权利的法律部门,对权利的限制,仅仅是例外情形。意思自治原则最大程度地宣示了民事主体行为的“自由”,这正是民法基本理念的体现。而公序良俗原则既然是从消极方面限制权利自由行使的例外规则,自然应该持“谦抑”的态度,不应积极扩张自己的范围。否则,便和民法“权利法”的本质相违背了。而且,公共秩序多规定或体现在公法、社会法领域,其仅仅是民法这一私法规范体系的补充,公共秩序的范围过大,可能会有“喧宾夺主”之嫌。
我们注意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完全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在近代以来走向衰落,但其仍为民法最基本之原则。而且对该原则的限制本身,其立意也是为了更好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如有学者在分析法国法上意思自治原则衰落时,列举了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形式主义复兴、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兴起等表现形式。[6](33?36)但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不正是为了真正实现当事人权利吗?正因如此,无论有关“民法社会化”“私法社会化”的论腔何等激烈,学界仍然普遍认为,“私的本位”乃是“民法在制度转变中不变的信念”。[11]
易言之,对于限制个人权利自由的公序良俗条款,我们尤其应注意保持谦抑之态度,在将“新秩序”纳入其中时,应格外慎重。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无论立意为何,表现形式终究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须认真考量。环境法学者也承认,“基于民法和环境法的范式差异,绿色民法典对保护环境的价值是值得期待的,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冲击民法的固有精神。毕竟民法之为民法,是因为其旨在实现私人的意思自治,而非环保;个人主义是民法应予修正和进一步完善的理论范式,而不是被予以取代的对 象”。[12]
(四) 环境道德性质的考量:道德义务之债
笔者认为,虽然环境保护者“持论甚直”,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现阶段,环境道德更适宜的定位(至多)是道德义务之债。对于自然人而言,保护环境确实很重要,但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基于道德而产生的义务。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具有抽象性,但本质上仍然是法律规范,采用的是“法律”的调整方式。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调整方式,是存在区别的。
将环境道德界定为一种道德义务之债后,我们便需要思考,对这种自然债务,法律应采取何种态度呢?法律是最低标准的社会规范,而道德属于高标准的社会规范。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未必是违法行为,尽管它在价值判断上可能是“可以谴责”的,还可能会受到良知、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责罚。而基于正义、公平等自然法理念上的考虑,立法者将一部分道德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这些基本道德的实现。但道德法律化在有利于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也给义务人课以更重的义务,这里面同样应该有一个是否公平的考虑。若规定道德义务之债的效力太强,一方面对义务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道德与法律合二为一,法律也会由于脱离实际而难以执 行。[13]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义务首先且主要应受道德来调整。我们认为,环境道德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民众,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将其纳入民法规范范畴,可能并不合理,同时也难以收到实际效果。法律的事情法律来管,至于道德方面的义务,还是交给社会舆论等道德监督主体来管,这也许是更加合适的。⑨
(五) 环境道德的认同度考量:现时是否足以成为“公序”?
前文已经述及,(在一定假设下)环境道德只可能属于政治公共秩序的范畴,而政治公共秩序试图维护的是带“永恒”色彩的根本性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就像被称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石油一样,并非真的“完全不能更新”,而是这个过程需要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达到非常严格的条件。⑩具体到环境道德方面,其在人类意识中形成的时间还相当短。例如,“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但距今也不过30余年。而相比之下,诚实信用、家庭道德、人格尊严等得到公认的“公序良俗”,无不是历经了长期的实践与积淀,且建基于稳固的社会认同。
“公序良俗”之“公序”,意指公共秩序,既然是“公共”,就需要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度基础,否则,便不能成其为“公共”的秩序。我们认为,虽然从国家层面、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大量出现的环保团体看来,环境道德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但这个基础是否足够大、以至可以成为“公共秩序”之一种?仍值得研究。而且从现阶段情况看,答案恐怕是不容乐观的。
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社会分层现象较为突出,而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中作出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不同的。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人群,首先希望政府多发展经济,即便污染了村边的一条河流、一条小溪,他们可能也认为是“值得”的;而对于“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富人们,对较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偏好,可能使其更加乐见环境质量的改善。 更何况,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不同,乃至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有些地区的人们可能根本就还没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能认识到杀人等行为是不对的)。事实上,在当前政府和许多社会团体、部分知识精英高呼“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仍有不少人主张“中国仍然很落后”“经济高速发展仍是当前要务”,这种现象也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对环境道德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真正达到“公共秩序”所要求的认同度基础,人们认识上的差异仍比较突出。
总体来看,环境道德的产生时间较晚,尚没有达到足以满足公序良俗原则标准的认同度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让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原则范畴,至少在当前看来,时机尚不成熟。 (六) 公序良俗的地域性考量:与环境道德国际性的矛盾
公序良俗原则具有时空判断标准,“时间性”标准前文已多有论及,这里作一地域性考量。虽然当前各国在“何为公序良俗”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有趋同之势,但地域区别还是存在的。笔者认为,公序良俗条款本身,便因此而具有鲜明的“本国性”“主权性”特征。当然,法律本身便有主权特征,但笔者认为公序良俗条款在主权性上因其地域性特征而更加突出和明显。如有学者便意识到,“至于公共秩序,因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应当采用国家标准来进行判断”。[14]
而环境道德问题,明显具有国际性的特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要求在不危害全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各国内部各地区和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6](105)由此可见,环境道德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公平的问题,如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各国就碳排放问题反复博弈、仍达不成有价值的共识,便生动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公序良俗原则的国家性和环境道德的国际性之间,有直接而且明显的冲突。如果罔顾这种冲突而将环境道德纳入一国国内法的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内,将不仅带来理论上的不能自洽,而且会给法院可能的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七) 司法技术考量:法官可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如果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可能带来法官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在全社会对法官素质仍持比较消极判断的大环境下,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人们难以接受的。
在当前的司法审判中,法官对一些事实问题、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相对比较有限的自由裁量,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如果法院可以将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等作为公序良俗之一种,这种现象将会更加明显。因为,法官对于环境道德是否属于公共秩序之一种,便可能存在不同认识。现实条件下,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基本只能采用司法模式,而不会在立法中明定;而我国并无判例法制度,这导致法官面对类似案件时,可能基于不同背景、不同立场,基本在不受约束的条件下,自由作出判断。极端条件下,完全可能出现甲法官因赞同环境保护重要,而以环境道德乃公共秩序之一种而援引公序良俗条款;乙法官因更倾向优先发展经济而拒绝认同环境道德是公共秩序之组成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在前述认同度不够的现实条件下,贸然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范畴,可能给司法审判带来混乱。当然,相对前几点原因,本问题在理论上是最容易克服的(因为毕竟只涉及“技术”问题),但实践中是何种态势,就难以判断了。
易言之,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即便在理论上被学者们、立法者们接受,其在司法实践中仍可能面临上述诸多困难。而诚如有学者认识到的,“中国目前在公序良俗原则上暴露的问题,并非在于要不要设立公序良俗原则,而在于如何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实践并求得具体妥当的结果”,并呼吁“莫清谈玄妙之论”,而要“寻求解决之道”。[2](7)无疑,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中公序良俗范畴,比理论上不能自洽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其在司法适用中可能面对的“无法具体化”、进而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实践问题。这些实践难题的解决,尚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与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问题,笔者的基本结论如下:
其一,环境道德很重要,但不宜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如上文所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一定需要纳入这些理念。这里面涉及到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环境道德从本质上看属于道德义务之债,规定在民法中、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缺乏合理性基础。
其二,在民事法律中规定环境问题,可能带来实施中的“无效性”等问题;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同样可能因其不被适用而使有关条款成为“具文”。在其他部门法中规定相关制度、体现环境道德理念,从法律实施角度看也许更加合适一些。事实上,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已经给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合适的平台和框架。环境法作为一个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法”,包含了多种部门法规范,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法框架下环境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等综合规定,来实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这即所谓“更宽广的视野”。
其三,即便在所有条件都已成熟、民众对环境道德形成极高的认同度、法制发展也需要将其纳入民法规范时,我们也应该有步骤、有策略地循序渐进。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在侵权法中较多规定环境侵权的规范,并通过司法实践来使这些已规定条款得到遵守;然后方才在此基础上,考虑在“基本原则”部分规定诸如“绿色原则”之类体现环境道德的原则性规定;而由于环境道德与公序良俗之间的一些如上文所述的不兼容性(如国内性与国际性的矛盾等),即便在彼时“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笔者仍然认为在公序良俗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仍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这里所建言的“由具体制度向基本原则循序渐进”的立法处理,除更具可操作性之外,还具有一个显著的优点:法律适用原则要求法院判案时一般“不向原则逃逸”,这决定了基本原则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被适用频度很低,而立法时基本原则条款又格外容易“撩拨起民众的神经”,因此,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反之,若在具体法律制度中规定有关环境侵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多次援用相关规定,这种对法律条款反复适用的过程,就更能够培养起民众对有关规定的“奉行度”,提高民众环境意识之立法目的更有可能实现。这便是所谓“更耐心的步骤”。
在分析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公序良俗原则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对由此体现的立法进路选择问题,有两点简单思考。权且在此提出,以为引玉之砖。 (一)“立法偏好”现象之反思
笔者认为,学界似乎有对一切问题进行立法的倾向,这甚至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学者鼓励对某问题立法(或将某问题解释为现有法律已有规定),然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有权机关解释法律),再然后学者依据该法律(或该解释)进行解释、批评,(关键是)期许立法机关继续更新法律制度,周而复始。仿佛离开法律规定,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不可能的。
上述“立法偏好”现象的出现,原因大抵有三:一者,学者可藉此掌握话语霸权。试想,若是某学者“呐喊”导致立法机关决定对某问题立法,继而该学者又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其无疑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当然”成为该问题的“权威”。一俟学界对该问题认识产生争议,其大可以拿出“立法过程”甚至“立法内幕”来对争议“下结论”,该领域的话语霸权由此而生。二者,我国近三十年来快速“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进程,客观上导致学者们养成了这种“立法偏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三者,这也是法学学者习惯从“法”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思维惯性所致。
在传统民法、刑法等领域,这种“立法偏好”没有问题,因为传统民法、刑法需要规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可谓是“没法不行”。但对于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问题”,是否仍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尤其是“环境道德”等“现代性问题”,即便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实施起来恐怕也很有难度。况且,这类问题通过道德、社会舆论力量来规制,未必效果不好;而用法律手段来规制,其效果未必就一定是积极的。
(二) 立法者的选择:超前还是保守?
一者,法律的保守性要求立法过程不应太超前,试图通过法律制定来革新人的心灵,是一个美好得以至于有些虚幻的追求。立法应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上,否则,不仅仅会增加人们的奉行成本,也可能使立法目的根本难以实现。环境道德之重要性当前在我国尚未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甚至环境道德这种提法就不被很多人所认可。纵使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理念,也不能因此就“超前立法”,试图通过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来促使人们洗涤自己的心灵、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这种做法是因果关系倒置:应该是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提升之后,才有将其纳入公序良俗范畴的可能性;而非反之。当然,笔者不主张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范畴,并不仅仅基于是这一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二者,向法律制度中引人“先进”理念应慢慢“渗入”,而不宜贸然“植入”(甚至是强行“塞入”)。笔者主张通过民法的侵权法中的具体制度慢慢向民法中引入“环境理念”,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不具备一定社会认可度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不仅是于事无益的,而且可能使法律的有效运行受到负面影响。可见,即便是先进制度的引入,也是需要策略的。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大量引介人类其他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
注释:
① 如魏振瀛先生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公平、公序良俗原则,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0页。尹田先生认为包括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75页。董学立教授则将民法基本原则区分为正面构成与负面构成两个方面,前者即指意思自治,后者包括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力滥用禁止等,参见董学立:《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146?191页。
② 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民事权利保护、公序良俗原则;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徐国栋先生的《绿色民法典》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绿色、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法律补充原则,参见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官方层面,如“可持续发展”“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等口号的提出,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建设“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实践等,都体现了官方(至少在思想层面)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层面,环境科学、环境法学等学科的兴起,便从一个侧面彰显学者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④ 在晚近的各国民法典中,有将保护环境作为所有权的义务加以规定的趋势,如《哈萨克斯坦民法典》第1条第3款,《越南民法典》第268条。但这些国家的民法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目前来看仍十分有限。
⑤ 如《法国民法典》两次提及的“公序良俗”均存在基本一致的理解,即第6条(“当事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和第1135条(“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德国民法典》仅有“善良风俗”的表述,但学者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是为了保证人们有秩序的共同生活而必须达到的“最低道德规范”,因此,违反“善良风俗”就是违反“公共秩序”。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谢怀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日本理论也认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都是指社会妥当性,前者着眼于社会秩序,后者着眼于道德观念,但无法明确区分,应予统括。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⑥ 事实上,民法和经济学的某种相通之处便是认为“个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后,社会整体效益往往也能得到最大化”“国家只需要辅助发挥调整作用即可”。 ⑦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生态人”假设,参见胡军、蔡学英:《“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理性生态人”假设,参见徐嵩龄:《论理性生态人》,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24页;“道德经济人”假设,参见张银花:《“道德经济人”的产生机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理性生态经济人”假设,参见王左军:《时代呼唤理性生态经济人》,《中国林业》2002年第8期;“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参见刘思华:《现代企业生态经济革命论》,《生态经济》2001年第3期;等。
⑧ 《十二表法》第10表第2条规定,“火葬用的木材不得用斧削光”,第10表第5a条规定,“不得保存死者的骸骨并为之举行葬礼”,第6a条规定,“不得对奴隶的尸体浇油,在各种丧宴上豪饮,奢侈地奠酒,不得用太大的花环和用香炉焚香”,第6b条规定,“不得用药水洒在死者身上”,第8条规定,“死者不得用金饰随葬”。该学者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体现环保、资源节约的“绿色”规定。参见前引[5],徐国栋书,第208页。
⑨ 事实上,笔者认为,在环境道德层面,社会舆论等道德监督的力量,如果构建较好的体系,其效果未必不如法律管制,尤其是相对在民法基本原则中抽象规定环境道德,其收效可能很有限。
⑩ 石油历经数百万年始得形成,由于其耗时甚巨,故人类称之为“不可再生资源”,严格意义上说,石油是可再生的。
从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可发现这样的现象:生活水平较高的人群,对总统大选期间进行的“环保”议题更加关注;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卸任后积极投身环保事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否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我们这里的观点呢?
至于目前社会上主流意见高呼“可持续发展”、鲜见相反声音的现象,一个可能(但却不一定正确)的解释是:这种意见比较契合政府的观点,从而掌握了话语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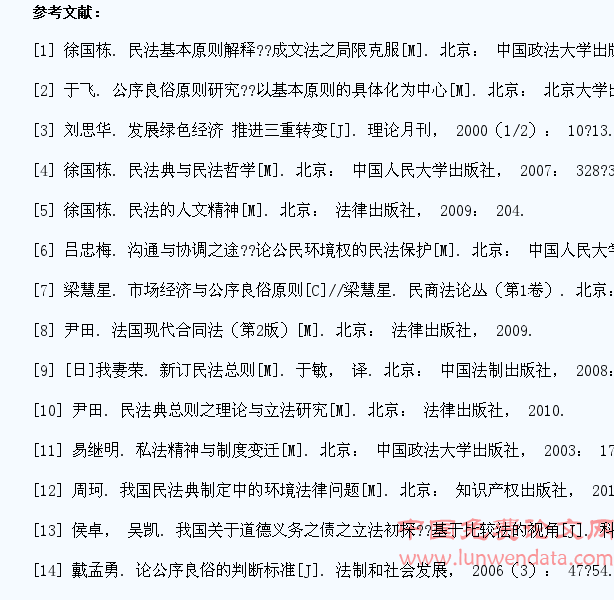
- 上一篇:我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述评
- 下一篇:论体育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