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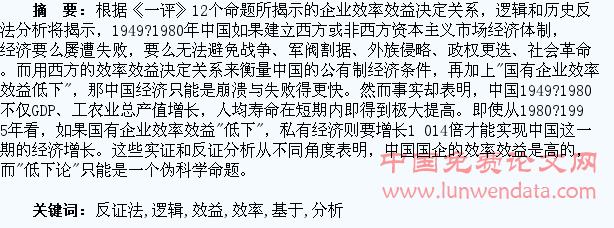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33-08
一、引言与研究方法
《一评》①根据西方要素理论和交叉科学方法,建立了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决定的变量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叉科学方法论框架下,运用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诺奖得主福格尔(Fogel,1962)的历史反证法(counterfactural historiography)衡量中国1949―1980年和1980―1995年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在科学假设、衡量、比较、反证基础上进一步证伪“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低下论”)这一理论。
历史反证法功能之一是通过对历史做同等或不等条件下的作用因素假设,用以检验决策、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及目的性。它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通过设定一个合理标准,检验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两种不同模式、决策的结果和效率效益差异性。从决策科学看,这也是一个信息完整性、实证科学性、选择优化性等博弈的综合衡量。
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反证法衡量不使用具体计量手段。第一,《一评》中12个命题的逻辑结构所表现的数理衡量方法本身已对封闭系统下简单、割裂、无视差异性的数量研究所产生的“低下论”做了证伪。第二,本文主要针对封闭系统下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validity)、可靠性(reliability)、适用性(applicability)、逻辑性(logicality)问题,而不是它们在实证分析中具体数量方法上表现的数理错误(尽管这种错误在方法论出问题时一般较难避免)。因此,反证法的运用主要是在《一评》12个命题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反证和历史实证主义反证推演出“低下论”的逻辑性、合理性、可靠性问题。第三,在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上,“低下论”逻辑如此荒谬,方法如此错误,结论如此颠倒,已远不是当年美国历史学家基于不当数据得出铁路不可或缺这一不精确结论的情况了。这就使得本文基于函数而非基于实证定量的反证分析具有其自身科学性。也因此,除运用福格尔的实证反证法之外,本文还运用逻辑反证分析。这个逻辑反证分析之成立,是因为它基于《一评》中12个函数关系的论证。
习近平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效率效益理论是针对西方市场条件下私有企业而提出的一个封闭系统。而“低下论”完全忽略这一条件,用割裂式、孤立式(即不考虑任何其他相关作用因素、条件因素以及各种差异性)这种极端封闭系统方法来把中国的国有企业与中西方私有企业做直接、简单、孤立的“利润”比较。②在相关实证过程中,这个“低下论”不会、不愿意也不可能运用科学方法对那些相关作用因素、条件因素及其各种差异性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处理从而使比较双方具有起码可比性。③这样,它必然扭曲历史事实,也必然存在比较衡量上的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我们在《一评》中根据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交叉科学方法产生的12个命题以及相应的指数化处理为不同制度下企业之间的效率效益衡量提供了可比性基础。这就保证了下面的逻辑与历史实证反证研究具有合理性、可靠性。它不仅证伪“低下论”观点,而且揭示1949―1980年间,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唯一出路。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思想,本文具有以下目的:在《一评》基础上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从不同角度证伪“低下论”;把颠倒的历史、事实、理论再用科学的方法颠倒过来。这个颠倒本身不仅重新证实中国1949―198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证实这个成就就是今天改革的经济基础之一,而且是改革指导理论与相关决策科学性的基础之一,是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之一。
二、逻辑与历史反证法衡量证伪“低下论”
(一)理论命题的逻辑反证分析与衡量
反证假设1:基于《一评》12个命题所揭示的企业效率效益的决定关系,假设中国1949―1980年建立一个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或类似“中华民国”的体制并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那么,根据西方经济学增长、效率效益要素看,从保证这个私有制下“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目的的实现看,从中国具有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素质低下(按照西方标准)的劳动力看,从中国当时拥有的资本存量看;从中国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看,从中国的人口规模看,从中国的人均可用资源看,从中国所需要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看,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与商的组织、文化结构的功能必然性看,从改革30多年来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特征看,④结果只有两种:要么中国1949―1980年间多次处于崩溃边缘,多次出现经济危机,多次产生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人口,多次面临“推翻萨达姆政权”式的军事侵略,⑤或多次出现社会动荡与革命;要么这个经济只有通过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与三座大山制度下相似程度的经济剥削与压迫,相似程度的贫富差别、两极分化、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才能维系,但那将无法避免战争、军阀割据、外族侵略、政权更迭和黎民涂炭。⑥ 反证假设2:中国1949―1980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集体为主,少量个体补充。假设:《一评》12个命题所揭示的中国资源、技术、资本、劳动力、人口、基础设施、国防和科技、价值观等因素与经济发展效率效益的关系成立;“国有企业必然效率效益低下”的结果成立;反证假设1的结果和“公有制效率低下”的逻辑成立,那么,中国经济将比反证假设1的经济失败得更快,危机更大,企业破产更多、更频繁;较1949年前与其说会发展,不如说会倒退;毕竟1949年之前中国的私有制程度远远高于1949年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业组织形式是私有制;官僚资本主义,尽管带有浓厚封建官商勾结色彩,也是私有制;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私有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础条件、西方效率效益决定、加上“低下论”的理论,中国1949―1980年间将产生全世界发展最慢、失败次数最多的经济。
反证假设3:1895―1945年间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城市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教育的发展,都相对同时期大陆的发展要快,企业效率效益要高。如果这里暂时把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放置一边,假设新中国建立后走台湾的道路,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由它来主导发展经济。那么,日本是否会给新中国带来台湾式的效率效益呢?台湾人口只有2千万,而大陆人口5.4亿,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为达到类似台湾1945年的发展水平,大陆需要等待1 350年。印度1949年时人均GDP是中国的1.5倍。中国是否可以学习印度的殖民地经验让英国来殖民呢?印度被殖民200年,其人均GDP不过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的1.5倍。中国以其更多的人口,由英国来殖民,那中国想要取得类似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只是200年了。而且,如果由日本和英国来殖民,即使某个资本家企业效率效益有提高,留给中国人民的又有多少呢?这种提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立志让“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那一代人不可能选择这种“效率效益”提高的方式和生产关系。
(二)历史实证的反证分析与衡量
上述逻辑反证分析揭示出那种“低下论”之荒谬性,而历史实证的反证分析将进一步揭示这种观点的伪科学性。为此,我们把新中国“一五计划”和1949―1980年间的GDP变化和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寿命变化作为纵向(中国自身发展比较)、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反证法分析的实证对象和衡量依据。首先,在一定条件下,GDP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综合效率效益的衡量指标之一,这个衡量也具有西方认可性。因此,1949―1980年间中国GDP(或工农业总产值)变化本身可以是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一种直观的检验,而且依此所做的反证分析将证明,如果中国不存在诸多不利变量因素,增长率会更高。其次,诸多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把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作为其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精神、物质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最强的衡量指标之一,而这个综合性又使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效益具有较合理的可比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以它作为三大因素之首)。
1. “一五计划”(1953―1957)期间的GDP与人均寿命变化。按不变价格计算,“一五计划”期间实际GDP/GNP年均增长9.2%(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按此速度实际GDP每8年翻一番(以私有制为经济特征的印度同期GNP增长率为3.4%,见刘树成等,1997)。⑦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提高到1957年的57岁,比当时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多15岁(迈克法夸尔、费正清,1990)。孤立地看,这个GDP增长率和人均寿命变化似乎平常,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性。但如果考虑到西方的要素理论和中国实际状况,考虑中国生产力水平、技术、资源条件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基数,也考虑到战争、国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再考虑到中国的保障所有人的就业制度,还考虑到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福利、保障、事业领域的基础发展与建设以及所需的庞大支出,再来看这个年均增长9.2%就不那么简单了,再来看这个人均寿命比相同国家高出15岁就不那么简单了,再来看这两个“不简单”的同时发生就更不简单了,如果再加上企业都是效率效益“低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反证假设1:中国上述成绩是在1949年极低生产力条件下取得的。假设:中国没有与世界上军事、工业、科技和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进行一场朝鲜战争;中国拥有那些任何一个“高效率高效益”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半的经济基础设施;中国在人口、资源、劳动力素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同、相似或接近;这个时期没有冷战,西方国家给中国送上的不是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战争与挑衅,而是投资和贸易的鲜花,是允许中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盛意,那么,按照《一评》12个命题构成的整体主义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一五计划期间是否会经济增长得更快一些,人均寿命是否会提高得更多一些呢?因此表现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是否会更高些呢?答案不言而喻。⑧
2. 1949―1980年间GDP与人均寿命变化。“一五计划”之后,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但工业总产值到1970年历史性地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1980年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初步实现了它原来所设想的发展目标。瑞赤曼(B. M. Richman)对中苏美印加的工业发展因素进行了详细国际和历史比较研究,指出1949―196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工业进步相对印度同期、苏联1918―1935年间的17年更大,与苏联1928―1940年间成就类似;⑨而且,如果没有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国GNP、人均收入、工业产出可能比1949―1966年间的实际值高出40%~50%,甚至是该实际值的两倍。即便在文革“十年浩劫”中,GDP年均增长率依然达到5.2%,⑩而工农业总产值年增率达到6.0%。埃克斯坦(A.Eckstein,1980)所报告的对中国1957―1975年间经济增长的估计由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出版,得出了与瑞赤曼类似的结论。{11}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中国1949―198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到9.2%。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经济实力薄弱、人均产值低下,但依然在生产力水平、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国防建设、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各类公益事业方面有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尽管这30年是艰难、曲折、复杂的30年,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内外部不利条件下建设、摸索的30年,是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发展与失误并存的30年,但决不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否定的30年。 再从人均寿命看,1949年中国为35岁,世界平均水平是47岁(1840年之后100多年间中国人均寿命始终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到1980年人均寿命67.77岁,而世界人均寿命56岁。1950―1980年期间,世界人均寿命提高29.9%;中国人均寿命提高88.9%。也就是说,30年间中国实现了人均寿命从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2年到领先9年共21年的转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规模、程度的人均寿命提高。图1表明,1970―1975年间,中国人均寿命接近65岁,而印度要再过30多年,即在2010―2015年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当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的中国人均寿命有这样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事业的发展无疑是重要原因,基本教育、卫生、住房等方面的改善无疑是重要原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生存的最基本经济保障是最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根本性、整体性、制度性的手段让中国人民的心理、生理、精神、身体压力与负担有史以来第一次降到中国历史最低水平。当时联合国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向中国学习(不是学习GDP年增长率)是不无道理的。
反证假设2:上述分析并不是说1950―1980年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挫折、错误、弯路。如果再从历史反证法看,假设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没有“大跃进”,{12}没有经历十年文革,中国在取得“一五计划”的成功后继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效率效益、打造并发挥自身优势,到1980年将是一个什么发展程度呢?即便发生了“大跃进”,自1961年初提出“八字方针”后,1963―1966年这3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15.3%,{13}而且已经开始一些“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带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尝试(如允许自留地、包产到户、责任制、发展小商品经济等)。按照这个速率推算,假设如果没有文革,中国1962年的GDP至少可以在1972年实现“翻两番”,而且在1988年达到2005年的实际GDP水平(提前17年),在1993年即可达到2012年的实际GDP水平(提前19年)。{14}
反证假设3:假设1981―2012期间中国: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科技水平远远高于1950―1980年,从而使急需发展、建设的相对投资比例降低;应对战争和威胁、加强国防等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降低其增长效应的领域建设的需求性、急迫性相对远远低于1950―1980年间,从而使经济发展可使用资本相对大大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不直接产生GDP效益反而降低其增长效应的事业领域基础水平远远高于1950―1980年,从而使国家支出比例相对大大降低;许多原来属于社会福利、保障等事业领域因商业化或准商业化而使全部(如住房)或部分(如医疗、教育、卫生、社保)等开支由劳动成员自己负担;劳动力综合素质远远高于1950―1980年,从而产生更高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没有经历1950―1980年时期“大跃进”“文革”长达13年的经济发展失误、干扰、阻碍,那么,根据1950―1980年总产值年增率与寿命增长率、学校增加率、入学增长率、住房改善率、医疗改善率、社保改善率以及这6“率”的社会平等性、公平性提高程度变化比例来计算、决定1981―2012年的变化比例,那应该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5}根据《一评》12个影响因素而构成的笛卡尔积空间[0,10]中,中国1949―1980年经济发展的条件相对西方应该收敛在[0,0.5]12中。假设中国1981―2012年的12个指数处于[2,4]的区间上,即使不考虑这12个指数的交叉作用,则它的可行集合的测度最少应该上升412倍。而且,这个[0,0.5]12到[2,4]12的转换、提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什么更能证明新中国前30年的效率效益所打下的经济基础、创下的资产、积累的资本正是改革30多年来效率效益的前提条件呢?为什么用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的效率效益来否定前者的效率效益呢?
(3)1980―1995年效率效益反证分析与衡量。在一个经济的效率效益衡量中,工业总产值变化是具有一般性的衡量指标之一。1980―1990年间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工业总产值比重中占90%,私有经济占10%。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70%,私有经济占30%(见表1)。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工业总产值变化不能不与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相关。改革开始后的1980―1990年、1991―1995年这两个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12.6%、15.7%,而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是否说明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呢?
反证假设4:为了证实即使在私有化进程开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依然是高的,不妨假设它们的效率效益增长率为0,企业数量因而不能增多,产量也不能增大,私有企业的增长要达到多少才能实现1980―1995年的增长呢?由表1可以看出,把国有、集体企业以外的工业产出全部看成是私人企业产出,则其1980年的实际产值为23.3亿元。假如国有和集体企业因效率效益低而从此后一直保持在1980年的4 772.7亿元的水平,于是,1990年的私人企业工业产值应该为8 396.0亿元,而1995年的私人企业工业产值应该为23 620.5亿元,才能实现实际的增长。于是,私人企业从1980年的23.3亿元分别增加到1990年和1995年的实际工业产值的水平,其增长率分别为360倍和1 014倍。也就是说,中国的私有经济在1980―1990年的10年时间里翻了8.5番,在1980―1995年的15年时间里翻了10番。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私有经济经历过这样的增长率。按照这个“效率效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要到中国来学习,而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可以为西方企业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设怎样发展私有经济的课程。{16} 以上对1949―1980年和1980―1995年的逻辑和历史的反证分析表明,孤立、割裂、简单按照西方封闭系统下产生的效率效益指标来比较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既是方法论上的东施效颦,又是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刻舟求剑、削足适履。它揭示出那种“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逻辑的荒谬性和“理论”的伪科学性。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要素理论为指导、以几个“私有资本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和宗旨、以剩余价值为手段(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剩余价值)下的私有企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为实证来做孤立、简单、割裂式比较从而论证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低下呢?真是数理分析和数量衡量的能力问题吗?否。{17}
三、结论:反证法分析与中国改革
本文的逻辑和实证反证法论证表明,根据《一评》12个命题所揭示的企业效率效益的决定关系、中国基础条件、西方效率效益决定,中国1949―1980年无论是建立类似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中华民国”的经济体制并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都将是全世界发展最慢、失败次数最多的经济。还是根据这12个命题所揭示的效率效益的决定关系、中国基础条件、西方效率效益决定,当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低下论”再成立的话,那这个时期的发展应该失败得更惨重、更迅速,经济发展应该远远落后于1949年之前。{18}在此以中国“一五计划”、1950―1980年这两个时期GDP、人均寿命的实际变化为实证对象的纵向、横向反证法分析证实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效率效益,而且,如果在西方效率效益决定的条件方面中国有世界平均基础水平,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这13年的干扰,如果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面临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战争威胁,这个“效率效益”变化的可预期结果将使得“低下论”更加荒谬。自1981―2012年的32年时间里,考虑到中国在12个效率效益命题的指数条件上远远优于1949―1980年(这个“优于”首先来源于1949―1980年,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在“大跃进”和“文革”的干扰下,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高效率高效益发展与积累),考虑到这期间没有“大跃进”“文革”等干扰,再根据1950―1980年总产值年增率、寿命增长率、学校增加率、入学增长率、住房、医疗、社保改善率这6“率”以及所体现的社会平等性、公平性提高程度,可以反证计算、决定1981―2012年的相应变化比例。它表明,中国前一时期的效率效益并不低下。如果“低下论”成立的话,1980―1990年、1991―1995年里,中国私有经济必须分别具有匪夷所思的翻番(即10年翻360倍、15年翻1 014倍)才能实现现实中的总产值增长。这反过来证明,即便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也是无法否定的。
显然,本文的逻辑和实证反证法分析证实了“低下论”的荒谬性和伪科学性。同时它和《一评》效率效益决定分析一起使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使1949―1980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没有发生危机,反而在发展上超出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预测、预料,不仅与“低下论”截然相反而且取得了令西方也承认的成就呢?这是一个今天与中国发展实践结合性极强、对中国发展方向与性质具有指导性的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强调要“实事求是”。因此这也是中国今天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进程中敢不敢“实事求是”、有没有信心、信念和理论基础去真正建设、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性问题。
本文的逻辑和实证反证法分析仅仅是针对1949―1980年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展开论证,不是用来否定改革。恰恰相反,这个分析证实了三个理论概念:第一,中国的任何改革手段、措施、方法、政策不应该建立在对国有企业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实事求是的否定之上,否则经不起历史检验、实践检验。第二,如果按照《一评》的12个命题来衡量,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可谓奇迹。而没有这个效率效益“奇迹”就没有1980年后的改革基础和条件,即便按照西方效率效益要素来衡量也是如此(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在衡量、评价中国国有企业时采用的是科学、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与国内一些研究大相径庭)。第三,中国今天改革中的政策、理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加以检验、衡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了人类历史和平时期少数人暴富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记录(龙斧、王今朝,2013;2012ab;2011)。而这些记录决不是也不能用来证实私有化、私有制的效率效益。毕竟,从经济综合结构、现代设施以及产生的效率效益看,从技术能力与手段及其效率效益看,从现代管理素质与水平及其效率效益看,从市场机制能力、合理性程度及其效率效益看,从资本条件、结构及其效率效益看,从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效率效益看,以及从这些要素结合所产生的综合效率效益看,中国1981―2012年的私有企业资本条件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但前者的私有资本增长率、资产增加率远远超过了西方企业。如果这些增长率、增加率可以用来证实“效率效益”的话,那就应该请西方企业及资本家都到中国来学习私有企业怎样提高效率效益了。另外,这种“超西方”资本增长、资产增加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19}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果,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结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是因为中国“出售转让政策”让少数人在一夜间“无本万利”呢(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是否因为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1949―1995年)在高建设、高发展、高积累、低工资、低收入、低生活(“三高三低”)条件下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资产、资本、资金一夜间沦为少数人所有并成为后者的原始积累呢?是否因为这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1949―1995年)在“三高三低”条件下建设的现代经济基础设施实际上为少数人的私有资本产生了相对最大的使用价值呢?是否因为本来属于中国所有劳动成员共同占有、平等享受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所产生的价值创造也首先为私有资本所占有呢?所有为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价值创造的劳动者在提供了、创造了使用价值后,得到的是一份工作,私有资本得到的是什么呢?在这种生产关系结构中,又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在这些条件和前提下的效率效益“高”又是为谁而高呢? 福格尔和另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对美国南方奴隶制农业和北方的个体自由农业做了比较,结论是,美国南方资本主义企业式奴隶经济制产生的效率效益远高于其北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农业(Fogel and Engerman,1974)。然而,它并没有阻止美国人民、进步人士、思想家、政治家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力量出于人权、人性、人道和道德原因打倒了这种高效率高效益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对美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调查中,72%接受这一结论。{20}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经济发展史上150多年前打破“效率第一,兼顾公平”概念的社会进步性尝试,{21}也是美国生产关系的进步最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极好案例。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体系上,它与龙斧、王今朝(2011)关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与社会进步、和谐不存在线性关系的理论结论有相吻合之处。{22}
鉴于本文反证法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和它所论证的三个理论概念,有人会问,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呢?当然要,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要怎样的改革(龙斧、王今朝,2013)。首先,改革二字本身是中性词,古今中外都用。因此,不能谁都自诩“改革者”,其价值观、观点以及所提出的模式、方法、手段就一定正确,不容讨论。如果把与己不同的人,或把分析、揭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矛盾、冲突的人,统统定为改革的“流言者、非议者、挑剔者、苛求者”,那就缺乏平等、民主讨论的精神了。如果再给戴上“阻碍改革”的帽子,那就与“文革”方法没有什么区别了。中国的改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两个原则缺一不可。以“有勇气、敢承担的改革派”自居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改革价值观、观点、思考、方法、手段就与这两个原则相一致;而把与己观点不同者定为改革的“反对者、挑剔者、苛求者”也不足以证明后者观点就违背这两个原则。
其次,从以下几个方面看,改革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在对苏联模式引为戒鉴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国以后经验教训基础上,就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提出既以工业化为经济发展重点,又要发展一定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毛泽东就曾提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这就是一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第二,关于非公有经济,毛泽东辩证地、比喻式地、调侃式地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再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同时提出可以搞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邓子恢就提出农村承包责任制;到60年代初,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更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下对农村试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第三,陈云在八大上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理论并获得赞同:以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的工商业,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以计划经营为主体的工农业生产,和按照市场变化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以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为国家市场的主体,和一定范围的、国家可控制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经济理论以及相应的实践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第四,周恩来1954年就逾越冷战意识形态、东西方对垒这个藩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23}第五,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尤其明确了对“第二世界”(即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文化关系。这五大历史背景奠定了中国必然走改革开放(如果西方也对中国开放的话)的道路,表明了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也是必然的,而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具有中国“以人为本”特色(而不是以GDP为本)的改革。
这样看来,本文对“低下论”的证伪以及因此产生的上述理论概念,对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与目的,对其“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解至关重要。首先,从目的性来看,改革具有两大目的性,一是纠正“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如当“文革”进行时,生产和正常经济制度运转必然受到影响,而劳动者却不断增加,那就必然出现“大锅饭”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二是中国已经建立了工农业基础设施、国防科技,不再受到战争威胁,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初步建立,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发展商品经济,把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体制转向公平性、平等性、正义性更强地改善、提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其次,中国需要探索在一个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相比西方)、技术能力极为落后、全世界人口最多条件下怎样使最大数量人口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而且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的方向和性质所在。最后,改革应该让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通过以我为主、有选择接轨和融入来达到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壮大、强盛的目的。非此,“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改革性质难以保持。
注释:
①在本文中,《一评》指龙斧、王今朝在本期杂志另一篇文章《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
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国研究与西方那些客观、科学的中国效率效益方面的研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参见Riskin(1987),Richman(1969),Eckstein(1980),Robinson(1973,1975)。
③这与它在“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在封闭条件下对增长要素进行数理数量分析时所表现出的高超能力截然相反。这恰恰说明,当意识形态和方法论极端化(如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公有制不能发展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等)作祟时,科学本身的严谨性已经不重要了,而数理数量工具就成为意识形态恣意妄为的魔方而已。
④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官商勾结具有这样的作用因素和特征:(1)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结构、文化、行为特征的影响(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寻租行为在本质和表现形式上都不同);(2)私有制价值观、文化土壤;(3)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是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时期的价值观影响后出现的。这里的反证假设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推理:中国尽管经历了1949―1980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改革后仍然出现了程度、规模和手段空前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如果按照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的“理论”,1949年起中国就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再把改革后的官商勾结搬过去,再把1949―1980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影响抽掉,那结果只有本文所阐述的这两种。关于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分析见龙斧、王今朝(2013,2012ab;2011)。 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西方入侵它国的理由之一。但美国为什么不以之为借口入侵苏联呢?前苏联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还是这种武器比伊拉克少呢?
⑥无论是1949年还是今天,中国都无法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类似“中华民国”的制度,那无非是用新的三座大山代替旧的三座大山,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依然会出现,也就会再出现各种剥削压迫,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依然会是他们的指导理论。如果中国今天搞极端私有化,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细致入微、无孔不入的封建制度所固有的文化、意识和政治、经济行为方式、手段模式就有了死灰复燃的土壤、空气和水分,集中体现在官与商、官与官、商与商、官与民、商与民的关系上(这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几千年,在到1949年之前,无论生产力怎样发展,朝代、政权怎样更迭,生产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封建”一致性始终不变)。由此封建模式、私有制和官商集团所形成的三位一体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典型社会特征。而毛泽东一代人真正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与实践、行为相一致的指导理论使他们选择了一个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社会制度,也因此,全国人民才可能与他们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关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分析,见龙斧、王今朝(2011)。
⑦有人认为,中国1949―1980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因为基数低。但这些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49年以前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更低。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只能说明是生产关系进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⑧当然,持有“公有制、国有企业必然效率效益低下”观点的人们立刻会找出各种理由说,这样比较不合适,中国基础低下,所以没有可比性。但为什么把基础不同、目的不同、性质不同、组织结构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条件不同、操作模式不同、劳动力组织形式不同、效率效益衡量标准不同的1949―1980年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还是带有封建色彩、官商勾结运行模式的私有企业)在孤立、封闭、割裂条件下按照西方理论所设定的利润指标来进行比较就合时、就有可比性了呢?这种因意识形态作祟、方法论极端化产生的“双重标准”难道仅仅因为加上了一点“东施效颦”式的数理数量研究及其所谓的模型就具有“科学性”了吗?关于这种“双重标准”的问题及原因见龙斧、王今朝(2014b)。
⑨相比今天中国众多研究所有制与企业利润率关系的文献,Richman研究企业效率的方法显然具有科学性优势。Richman,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p. 596.
⑩以1952年GDP为100,1966年和1976年GDP不变价格指数分别为237.1和392.2(《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由此计算出的复利增长率为5.2%。
{11}参见该书第11页关于总产出、第20页关于谷物产出、第24页关于农业产值、第26-27页关于工业产值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取得了高增长成就。
{12}“大跃进”主观愿望对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现状和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针对性,但其方法、手段违反“科学发展观”从而不具有实践指导的科学性。然而,“大跃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社会人群根本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矛盾并未产生,因而只是经济政策失误而已。也因此,“八字方针”可以较快地使中国经济发展重新回到自身轨道和规律中来。详见龙斧、王今朝(2011)分析。
{13}根据表2数据用复利法计算。
{14}以1952年GDP=100,则1962年GDP=140.4,2005年GDP=5 677.5。然后从140.4×(1+15.3%)n=5 677可以求得。所以,按照这三年的增长率,1988年就会达到2005年的发展水平。
{15}当然,“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论者立刻会找出各种理由说这样比较不合适。但为什么这时就考虑因素差异性及其作用,而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衡量时就不考虑差异性因素,而只是简单、孤立地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将它们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下或官商勾结下产生的私有企业进行简单对比从而得出荒谬的“低下论”来呢?
{16}中国一些私有企业、老板、“精英”也因为“一夜暴富”效应而的确具有这种“中国效率效益远远高于西方”的心态。一个私人老板在电视上宣称,诺贝尔奖得主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能像我们(私有企业)这样养活这么多人吗?能创造出我们这样的经济效率吗?而实际上,许多中国私人企业增长的原因至少包括:(1)新中国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在高建设、高发展、高积累、低工资、低收入、低生活(三高三低)条件下艰苦创业所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在出售转让过程中无偿或极为廉价地交到了私人老板的手里;(2)新中国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在“三高三低”艰苦创业所积累起来的资产、资金、资本首先是用来满足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私有企业的发展;(3)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创造、产生的少数人超常“效率效益”;(4)人类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里最庞大、素质最高又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即便是美国资本主义奴隶经济制的“少数人”都没有上述(1)、(2)两个条件。毕竟,那是在两千万奴隶、在原始条件下为美国资本主义创造的原始积累。这就解释了美国最富有的人群是在300年间实现其今天的富有,而中国的少数人在人数规模和富有程度上只用了30年就达到了美国亿万富翁的水平(毕竟几亿人、几十年在“三高三低”条件下的积累远远大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种超出西方的“效率效益”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因。
{17}直到今天,中国还在摸索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把它作为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根本性质。然而在客观上,在这种“低下论”伪证支持下产生的政策使中国99%的国有企业未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效率效益的实践和时间过程,本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摸索、建立的最主要、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标志性的任务和理论内涵。如果企业都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又从何谈起呢?依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把这一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搞清楚,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性质的大问题。 {18}照此“低下论”逻辑,新中国的成立简直就是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当1989年苏联解体时,持有“冷战思维”的西方专家这样评论到,俄罗斯民族终于从70多年的社会主义梦魇中苏醒过来。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观点似乎在表明,原来的沙皇俄国是无比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的平等、公平、正义社会,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把它推入了梦魇!
{19}1956年完成的新中国对资本主义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考虑到12个效率效益的变量关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理论,1949―198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而对国有企业的出售转让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规模、程度、速度看它是一次全面的对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2009)。在“最初级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到“初级阶段”再通过贱卖转成私有企业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毕竟,这种理论和逻辑上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20}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Fogel。而在那些(28%)不同意Fogel-Engerman范式的学者中,多数是不同意美国内战的目的首先是出于解放南方奴隶,并非不同意他们关于美国内战前南方资本主义企业式奴隶经济制产生的效率效益高于其北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农业这一概念。
{21}欧洲、加拿大打破这种高效率高效益的资本主义奴隶经济制较美国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这才有了美国奴隶的“北上征程”(“Northern Expedition”)。
{22}龙斧、王今朝(2011)一书论证了不是经济增长和GDP,而是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状态与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的一致性程度决定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程度。
{23}“改革开放”的“开放”概念常常让人以为1949―1980年中国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先进、夜郎自大的国家。而事实上,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60年代提出“向西发展”;70年代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强调要与西方第二世界国家进行教育、科技、贸易等往来。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是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战略包围、扶持台湾、武装日本,不是中国想与他们搞开放,它们就会开放的。因此,改革开放的“开放”概念更多地是指解放思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模式,指的是思想、理念对单一经济体制的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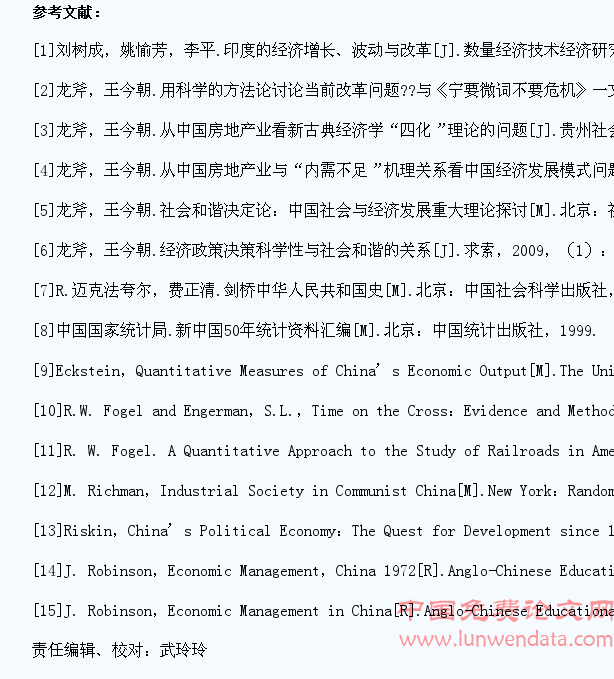
- 上一篇:浅谈企业青年党员如何走好群众路线
- 下一篇:公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难点与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