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通:庄子“道通为一”的哲学阐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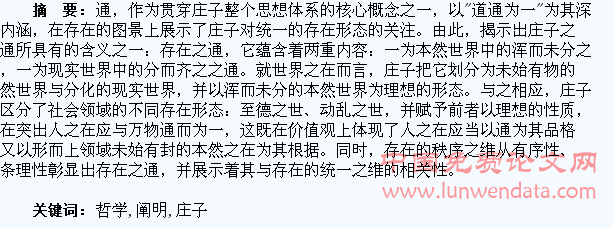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15-007
通,作为贯穿庄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以“道通为一”为其深沉内涵,在存在的图景上展示了庄子对统一的存在形态的关注。由此,揭示出庄子之通所具有的含义之一:存在之通。就存在的图景而言,在庄子那里有着两种世界图景:其一为未始有物或者未始有封的本然形态,其二为分化的现实世界。具体而论,未始有物或者未始有封的本然形态,即超然本体论上的有无之分、时间上的先后之别的本然之在,亦被理解为玄同的世界、原始的混沌:“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这种本然的存在作为世界的原始之在,呈现的是浑而未分的统一形态,具有已然与应然的双重特征。这种存在图景既是世界的原初存在形态、本然世界,又表现为世界之在的理想形态。相对于本然之在,分化的现实世界作为存在的既成形态,以“分”、“异”为特征:“万物殊理”、“四时殊气……五官殊职。”(《庄子?则阳》)显然,这种存在图景并不合乎庄子的理想,但它作为存在的现实形态、现实之在,具有实然的特征。与存在图景的分疏相应,存在之通亦表现为两重内容:一为本然世界中的浑而未分之通,一为现实世界中的分而齐之(1)之通。这亦可看作是“道通为一”的具体化,它分别呈现于世界之在与人之在之中,同时又内蕴着秩序之维。
一、世界之在:本然世界与现实世界
在庄子那里,世界之在有两重内涵,其一为本然世界,其二为现实世界。由现实世界出发,向前追溯,直至世界的原初存在形态:“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始”即开始,是宇宙在时间上的开端。由“始”这一开端向前追溯,达到的是未曾开始的开始,再向前追溯,则至于未曾开始那未曾开始的开始,即达到了“天地之始以前之再前”[1]72。换言之,由现实世界之时间上的开端向前追溯,最终达到的则是存在之无始或无开端,而这种无始其“本体论意义是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它意味着存在的终极形态或本然形态无时间上的先后之‘分’”[2],也就是说,存在的这种无始扬弃了时间上的先后特征,从而在实质上亦消解了时间之维。同样,现实世界纷杂、多样的现象呈现出“有”、“无”的分别,由之出发,向前追溯,达到的是“有”、“无”都不存在的形态,再向前追溯,最终所达到的是超越“有”、“无”之分的“无”。现实世界之“有”、“无”是具体的形态之存在或消失,因而具有空间特征;与之相对,源始意义上的“无”扬弃了具体对象的“有”、“无”之分,从而在实质上消解了空间性。在现实世界中,时间维度上的先后之分、空间维度上的具体对象的有无,都是分、别的体现;与之相对,向前追溯所达到的世界的原初之在超越分、别,消解时间、空间,呈现的是世界的本原或初始的形态。唯其无分、别,所以世界的原初之在作为本然的存在表现为玄同的世界。[3]
显然,庄子的以上分析立足于分化的现实世界,通过逻辑的推论,从现实世界直至浑而无分的原初之在。原初之在之原初性,说明其已然的性质,而对庄子而言,现实世界之既成性、现实性,赋予其实然的特征,构成庄子不能不面对、不能不生活于其间的存在形态。当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的世界时,多样的形态便得以展现:“万物殊理”、“四时殊气……五官殊职。”(《庄子?则阳》)“万物”确认了物的多样性,“殊理”则彰显了物之为自身的特殊性;“四时”之“殊气”、“五官”之“殊职”则从自然到社会均确认了多样性、差异性。
然而,就分化的现实世界而言,在多样的形态背后,实质上仍然以“通”为其内在特征。
首先,这表现在庄子对“气”的理解上。“气”在庄子那里,对应的是分化的现实世界,并只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杂乎芒芴之间”与“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泰初”一样,是对世界原初形态浑然一体的表述。“变而有气”表明“气”产生于原初之在。就形而上的层面来看,“气”具有质料的性质,从而赋予“气”以“有”的特征,即获得了某种具体的规定。在有“气”的基础上,由气作为质料,物之“形”才得以产生,由此衍生出天下万物。因而,就“气”之产生意味着“有”之产生而言,“气”展示了其与原初之在的疏离,并确证其与分化的世界之在的关联。尽管“气”是“有”的一种形态,但“气”与万物之“有”却不相同,作为万物形成的基础与质料,“气”具有“一”之特征:“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天下万物,不管是“神奇”所表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事物,还是“臭腐”所指涉的具有负面价值的事物,均由“气”构成。而“通天下一气”既确认了“气”在质料的层面构成万物,又确认了“气”之“一”,就此而言,可以说万物“一”:“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庄子?田子方》)与此相关,“气”之“一”既蕴含着自身之通,又赋予万物以通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万物在质料的层面通,另一方面又使得具体世界中不同的存在形态之间在彼此能够相互转换的意义上通。相对于世界的原初形态,分化的现实世界最先具有的“有”即是“气”,并进一步展现为具有多样存在形态的万物,但“气”之“一”、“通”使得多样的事物在呈现各自独特性的同时,彼此之间又并非隔绝和分离,而呈现出通之维。对于庄子的“气”,刘笑敢曾说:“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气”,“气是万物存在变化的基础,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但是气远不如道重要”,“庄子自身的逻辑应该是气由道生,道为气本。”[4]136同时,他分析了庄子在其哲学体系中引入“气”这一概念的原因:“首先,在无为无形的道产生具体有形的万物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状态。其次,庄子是强调齐万物而为一的,在物质世界之内需要一个体现万物共同基础的东西。最后,庄子是强调事物的相互转化的,需要一个能够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的概念。适合这些需要的概念必须是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可以运动也可以凝聚、可以上达于道也可以下通于物的,这样的概念只有气。”[4]137 其次,庄子对道的规定亦展示了现实世界之通。在庄子看来,道构成了世界之在的根据,并内在于不同的存在形态之中。就世界的原初之在而言,其表现为浑而未分的原始统一,这种存在形态可以看作是“道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的呈现。“封”即界限,“未始有封”表明道没有分际、界限,以统一性为自身的内在品格。刘笑敢指出:“‘道未始有封’即说明道是外无界限、内无差别的,因而道是绝对的同一。‘道无封’的特性是庄子预设的齐万物而为一的客观依据。”[4]113“未始有封”之道作为世界原初存在的形上根据,在此,道之通主要呈现的是其未分化性、无界限性、统一性。
在分化的现实世界之中,道“无所不在”:“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万物之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但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物之中。庄子与东郭子关于道之在的对话清晰地展示出这一点:“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不管是蝼蚁、?稗、瓦甓这些价值形态较低之物,还是屎溺般具有负面意义的事物,道都内在于其中,“无所不在”体现的就是道的这种普遍性。而在“万物殊理,道不私”(《庄子?则阳》)中,“殊理”是使物在本质上成为其自身的形式规定,从而将物与他物区分开来,“万物殊理”表明不同之物具有不同的规定,而与之相对,道之“不私”意味着道超越具体事物之异而具有普遍性。因而,作为存在原理的道,在分化的现实之在中,其通主要呈现的是普遍性。但是,道对于万物之“无所不在”并不意味着道之分化,道之普遍性背后隐藏的是其统一性:分化的世界中,道仍以统一性为自身的内在品格,并呈现于一切对象之中,使得每一物均有自身的存在根据、本原。于连指出:“世界的多样性,从小草到大檩,从丑女到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可’,但是,‘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所以‘道通为一也’。因此,‘道通为一’远没有导致万物的趋同和贫乏……这种统一……是贯穿性的统一,同时也是过程性的统一。”[5]
因而,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作为存在本原、根据的道既具有无限唯一性,又具有无限包容性;既超越于万物之外,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既在原初之在中,又在现实之在中,它同时跨越世界之在的这两种图景而伫立于其间:道以其统一性、普遍性赋予世界原初之在与分化的现实世界以通的特征,又成为两种世界之在的形态具有连续性的形上依据。
二、人之在:人与万物为一
世界的原初之在分化为具体的世界,万物得以产生,在这一分化的过程中,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亦获得了存在性:“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就“气”作为万物形成的质料而言,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无疑以“气”为构成人自身的基础,庄子用“气”之聚、散解释人之生、死,即突出了这一点。同时,“德”作为道在具体事物之中的体现,亦呈现于人,并表现为人之为自身而异于他物、他人的本质规定:“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之“物”即包含人在其中。就此而言,人与天地间之万物通而为一:“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作为世界的具体的呈现形态,是原初之在分化后的产物,而“我”作为类之人,其产生一如“天”“地”之生成,是世界原初之在之分化,由“气”构成。对应于世界之在之分化过程,可以说,“天地”与我“并生”,而推广开去,亦可说,具体世界中的一切存在形态均与我并生。然而,与我并生之万物的呈现形态各异、大小有别,如秋毫通常意义上意味着“小”、泰山则代表着“大”;人之生命亦长短有别,如殇子之短命而“夭”、彭祖之长“寿”。但是,在庄子看来,大小、寿夭等具体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区分、差异,并不构成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间的绝对界限,在天下万物都“一”于气、内含“道”的意义上,可以说,万物通而为一,进而言之,人亦与万物“为一”。
人与万物为一,同时内蕴着人与人通而为一的维度:首先,就作为类的人来说,从人之获得生命为气之聚、生命结束为气之散来看,人之生死呈现为气的聚散。唯其统一于气,因而人之生、人之死这两种不同形态之间具有了能够相互转化的根据,从而表现出生死相通。
其次,就个体来说,不论是如殇子般短命,还是如彭祖般长寿,不同之人均需经历从生命开始至生命结束的整个历程,不管该历程是长是短,从过程及最终的指向来看,人与人之间在由生走向死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在如下论述中得到了体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庄子在其妻死后,对人之生命存在向前追溯,直至无形、无气、浑而未分的世界原初存在形态,展示人作为万物之一,其生与万物一样,产生于原初之在的分化:“杂乎芒芴之间”即是对世界原初之在浑然一体的表述,亦即“无气”的原始之通,而由无气至有气,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世界,再至“有形”,“形”在此指人之形所表征的人之生命存在的获得,接下来,由生至死,即人之生命的终结,人之生伴随着世界之在的分化,并如同春秋冬夏四季的交替,这使得人之生、死成为世界之在演化过程中相继的两个环节。因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生、死相通。由此,人之由生到死既表现出自然性,又具有必然性:人之死意味着人之生命存在的终结,而由生至死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就人与万物的关系来说,人之死虽意味着个人生命的不复存在,但他又是万物中之其他物形成自身的质料:“子来……将死……子犁往问之……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庄子?大宗师》)“以汝为鼠肝”、“以汝为虫臂”十分形象地表明子来死后,可以作为“鼠”、“虫”等自然之物的构成。在这里,庄子将人的生命置于世界之在的链条之中,使得“生”“死”同时融于万物之中:“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庄子?田子方》)就天下万物来说,作为“气”的不同形态,生、死如同昼夜的更替,表现为一个循环的过程。毋宁说,作为个体的人之由生走向死的背景、前提是天下万物之生、死的相继、循环。 再者,就个体来说,存在形态不同、精神境界不同的人,均由气构成,从质料的层面来看,人与人通;从人人体现道、人人具有“德”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亦通。
事实上,人与万物的合一,在本体论上体现着世界之在的普遍相关:不管是人与万物通而为一,还是人与人之间相通,都肯定并确证着这一点。陈鼓应曾作了如下论述:“从哲学观点来看,庄子是从同质的概念去看待人与外物的关系的。……就是说,人与天地万物的原质是相同的。因而从同质的概念出发,庄子认为人与外物、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隔离的,而是一体的、合一的。”[6]
人与万物之通还体现在价值论的层面。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如果没有人之在,价值之维亦不会存在。就价值论来看,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突出地体现在社会领域。庄子区分了社会领域的不同存在形态: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就至德之世来说,其特点是人与万物合而未分,因而,庄子把它作为理想的存在形态,以“至德之世”来表述即是对其理想性的肯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李勉说:“‘填填’、‘颠颠’押韵,同一意义,当时口头语也,自在而得意之词。言民之真性。”[1]247在此,用“填填”、“颠颠”形容人之“行”、“视”表明人的存在方式同于自然。而“蹊隧”、“舟梁”是人化之物,“山无蹊隧,泽无舟梁”则表现了外部世界完全停留在本然之在的状态。在这一本然之在中,人、禽兽、草木等万物都呈现出自在的形态。因而,在这种存在形态中,万物虽然已分化而出,作为类的人虽然亦生活于其间,但人与禽兽、草木等各自呈现出自在的存在形态。从整体来看,整个外部世界表现出的是未经人的任何变革的原初状态。显然,在这一原初状态中,人与万物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分化的存在,但在实质上,人与万物却以合而为一为其特征,这显然是“未始有封”的世界原初存在形态在社会领域中的显现。同时,在至德之世中,不仅人与自然之物合而未分,人与人之间也以无分为特征:“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无君子、小人之分即显示了人与人之间通而为一。以人与万物合一为特征的至德之世作为理想之世,内含着应然的规定:应当达到的理想形态。同时,它又是前概念的存在形态:“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羲)氏、神农氏……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箧》)“昔者”展示出以人的视角对历史的回溯,“至治”表明庄子对这种前概念形态的态度及评价。在此,对历史的回溯和评价赋予至德之世以理想性,又使得其与前概念形态合而为一,二者无疑都以未分化为特征。
然而,由人与万物合而未分的淳朴之世,走向“世与道交相丧”(《庄子?缮性》)的动乱之世,社会由“至治”而趋于“乱”。庄子认为这一历史演进的根源在于分、别,“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缮性》)。礼、乐即以分、别为特征。“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治天下”亦以人与天下万物之分为前提,表现为人对天下万物的作用过程。因而,以分为前提的“治天下”,只能是以“治”为名,而实质上却是“乱莫甚焉”。同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亦具有负面的意义和否定的价值:其既以分为前提和内涵,又具有外在于人的特征。与庄子一致,马丁?布伯亦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制度乃是‘外在的’,人于其间追逐种种目标……社会制度……是无灵魂的泥偶……不知人为何物……不能接近真实人生。”[7]37-38
可以看到,由至德之世的人与万物合而未分,走向动乱之世的分而别之,庄子立足于动乱之世而对上古以来历史演进过程的回顾,既是对动乱之世的现实性的表明,又把着重点落在对人与万物合而未分的理想存在形态上。就此而言,庄子在社会领域区分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其旨在突出人之在应与万物通而为一,这既在价值观上体现了人之在应当以通为其品格,又以形而上领域未始有封的本然之在为其根据。
三、存在之序
庄子以道为世界之在的本原、根据,既展示了存在之通,又内蕴着存在之序。“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庄子?天道》)即确认了道所蕴含的秩序之维。存在之通展示的是对统一性的关注,而存在之序则隐含着对条理性、有序性的要求。因而,庄子之道既展开为统一性原理,又表现为秩序原理。与存在之通一致,存在之序亦呈现于世界之在的两重形态当中。
就世界的原初存在而言,其由于未分化而展示出原始的统一性,同时,亦呈现出秩序之维:不论是与“未始有物”相联系的浑然一体,还是与“未始有封”相关的浑然无分,作为原始的混沌,其中所蕴含的统一性都使得它们与纷杂、无序无关,而内含着自身之序。但是,原初之在本身的秩序只呈现为有序,并具有隐含的性质,从而区别于分化的现实之在的秩序性。在具体世界中,其秩序性既呈现为有序性,又表现为条理性,并展开于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
就自然的层面而言,庄子以分化的现实世界为基础,对“道”所蕴含的秩序之维进行了分析。“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尤,尤而不救。”(《庄子?人间世》)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世界,便呈现为具有区分、差异的多样的形态。然而,当物与物之间的分际被过度强化时,世界之在便呈现为“杂”的形态,由之而来的则是“多”,这一意义上的“多”所体现的不是多样性,而是与纷杂、杂乱相联系的无序。就分化的现实世界来看,道作为存在的根据,其统一性、普遍性统摄着具有区分、差异的多样存在形态,赋予多样化的万物以内在的秩序。因而,“道不欲杂”既是“道”以其统一性对“杂”所体现的杂乱的否定,从而表现为对无序性的扬弃,又彰显出“道”所肯定的条理性、有序性。后者首先体现在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中:“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肃肃”即寒冷,“赫赫”即炎热,“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表明阴、阳是两种彼此不同且彼此对立的力量。[8]从万物的生成、演化来看,阴阳二者交互作用所体现出来的“和”,真实存在并使天地万物得以“生”。同时,这种“和”内在地蕴含着秩序之维,正是这种内在的秩序,使得万物之死生盛衰呈现出自身的法则,从而有规律可依、有理可循。因而,天地万物之生、之化,都非杂乱而无序,而是内含着秩序性。 在万物既生之后,天下万物与道的关系使得存在之序与存在的本原的关系得以揭示:“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作为“本根”之道,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本原、根据,而且内在地规定着天下万物运行的方式。在万物变化、运行过程中,正是内在之道,使得阴阳四时的运行呈现出有序性,使万物的变化展示出秩序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四时之“明法”、万物之“成理”都体现了存在的秩序性,而天地之“大美”在“美”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天地之间的有序,因为纷杂形态的天地万物呈现的是“乱”,而非“美”。
但是,分化的世界所具有的存在之序完全自然而然,从而不同于目的性的安排。每一物均具有自身特定的时空位置、因果网络,并“各居其位,各循其途,各具其可测度性及特定本性”[7]26。这在庄子“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的论述中得以体现。宽泛而言,分化的世界中天地万物、阴阳四时所具有的秩序并没有“怒者”使之然,其有序性、条理性完全取决于自身,自然而然,不假外求。
就社会领域来说,庄子确认了不同的存在形态:至德之世与动乱之世。在至德之世中,世界虽已分化为多样形态的万物,但万物之间却“未始有封”。与对自然层面的本然世界所隐含的秩序性的确认相同,庄子也确认了至德之世体现的是最完善的社会之序(“至治”)。与之相对的,则是非至德之世中社会的失序。从远古时期人与万物相融、人与人和谐到充满冲突、争战的动乱之世,庄子认为在“至德之隆”的“神农之世”之后,则是所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的非至德之世。在非至德之世中,人与万物逐渐分离、人与人之间充满争斗,社会则趋于“乱”,“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展示的就是社会的无序。
但是,在庄子那里,就社会领域而言,其秩序性既体现于至德之世,又需在非至德之世中实现。因为至德之世具有的已然的特征,指向的是时间的过去之维,尽管它代表着“至治”的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并作为理想的存在形态而指向未来的向度,但它终究不具有现实性。而非至德之世作为现实的存在形态,作为人不得不生存于其间、不得不面对的社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有序性,这从“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庄子?让王》)中庄子将非至德之世区分为“治世”与“乱世”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非至德之世中的“治世”之“治”不同于至德之世的“至治”,前者只是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秩序性,而后者则是最完善的社会之序。但就二者均体现着社会的有序性来看,则又有着相关性。由于“治世”呈现出有序性,因而对人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而“乱世”之冲突、争斗所呈现出的无序、失序,则往往会危及人的生命存在,因而呈现出否定意义。
同时,非至德之世之“乱”亦直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当社会呈现无序、失序的状态时,相争、相斗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存在方式,反映在个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当中,心灵的紧张、不安随之产生。与之相应,个体的精神世界呈现的亦是相互对峙、彼此排斥的失序状态。
人的精神世界的分化、失序,不仅是社会政治形态之乱的反映,而且也是观念领域失序的体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在此,“天下大乱”主要指向的不是政治上的失序,而是观念领域的分化、无序,它集中体现在由执著于一偏之见而导致的观念、意见的纷乱即是非之争上。“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是、非的形成,及执著于是或非,是对具有统一性的道的分裂。与之相应,是非之争表现为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相争、相斥,而“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庄子?齐物论》)则显示出是非之争所导致的精神世界的迷乱。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是非之争体现出具有不同观点的各方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执著与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情感层面的好恶,如对其所“是”的显然喜之好之,对其所“非”的则怒之恶之。这种喜怒、好恶之情的“失位”即偏失或无序,则将进一步引发精神世界的不健全,从而最终导致人之本然之性的失落。
因而,要扬弃精神世界的紧张、冲突,实现精神的平和、有序,既要求在政治领域实现其“治”,又要超越是非之争,并且合理安顿自身的情感,以维护和挺立自身本然之性。在观念领域,庄子以齐是非来扬弃乱而无序的状态:“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对庄子来说,精神世界的有序性即为“和”,所谓“心莫若和”(《庄子?人间世》)便确认了“和”作为“心”的存在形态,代表了平和之境。这种平和的心境既蕴含着有序性,又以“一”为指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也就是说,个体只有保持、守护其精神世界的内在的统一性,才能使之达到心灵平和的有序状态。在此,精神世界的统一性所蕴含的“一”之维,与心灵的平和、宁静所体现的秩序性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庄子对存在之序的关注,与世界之在的两重形态相应,在自然层面上既赋予世界之原初存在以秩序性,又通过分而齐之赋予分化的现实世界以内在之序;在社会领域中,既肯定至德之世所蕴含的自发之序,又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非至德之世中呈现的有序形态,而“治世”之有序性则为人精神世界之平和、宁静提供了担保。因而,不管是自然层面的万物,还是社会领域中的人的存在,当它们以条理性、绵延性、有序性为其存在的方式时,多样的存在形态之间不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相通、相互关联的。就此而言,存在之序既使存在的分离性得以扬弃,又使自身与存在的统一性合而为一。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之在的终极本原,“道”在庄子那里既展开为统一性原理,又表现为秩序原理,二者分别从统一性、普遍性与条理性、有序性的维度使存在之通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因而,存在的图景及与之相关的存在之通,所展示的是存在本身,换言之,即存在是什么和怎样是。就世界之在而言,在世界的原初存在形态中,其浑而未分的性质使得通显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作为形上原理的道之未分化及统一性则是这种存在形态之通而为一的根据;分化的现实世界既在质料的层面以“气”作为万物通的根据,又在存在根据的层面以“道”之普遍性赋予存在以通的特征(2);世界的原初之在与分化的现实之在作为世界的两种存在形态具有连续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连续性亦可看作是通的体现。就人之在而言,作为分化的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形态,人与万物的合一,则从人的角度展示着世界之在的通之维。同时,存在的秩序之维从有序性、条理性彰显出存在之通,并展示着其与存在的统一之维的相关性。
注释:
(1)分而齐之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维度。在此,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分化的现实世界以区分和差异为特征,在自然的层面,其具体展开为万物;在社会的层面,又展开为纷杂的社会现象及更替的社会形态。但以“分”和“异”为特征的现实之在却仍具有通之特征,并有本体论上的根据。换言之,表面上,现实之在呈现为相分的万物、纷杂的社会现象及社会形态,而从实质的层面来看,现实之在不仅以通为根据,又以通为指向。就此而言,现实之在彰显出分而齐之的本体论维度。
(2)就分化的现实世界所具有的“通”的特征来看,刘笑敢认为“在庄子哲学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气的世界,万物不过一气,气不断聚散游移,物则不断起始生灭,所以现实世界是纷乱的、运动的、相对的”。(刘笑敢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这一看法虽然有见于现实世界在表面上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变动性,却忽视了具体世界本质上所蕴含的通(包括秩序)之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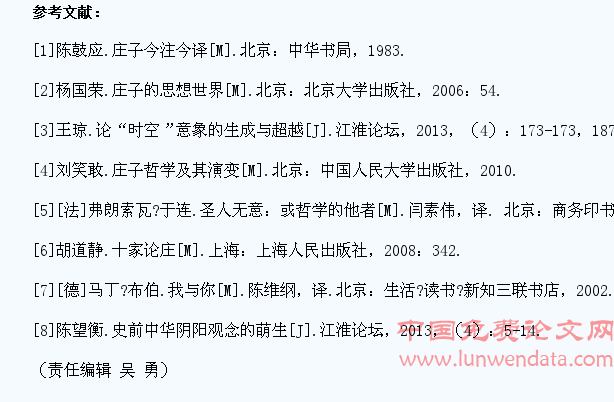
- 上一篇:梅洛―庞蒂身体哲学视域中的画家视看问题
- 下一篇:以哲学自觉支撑生命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