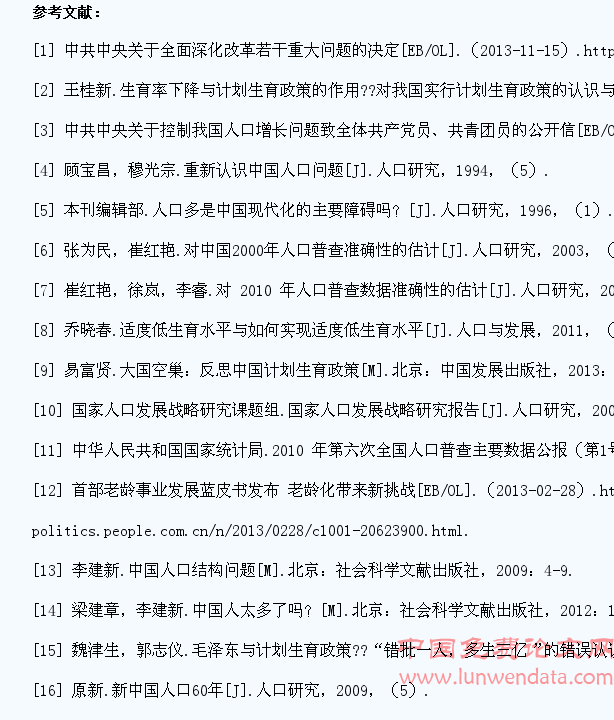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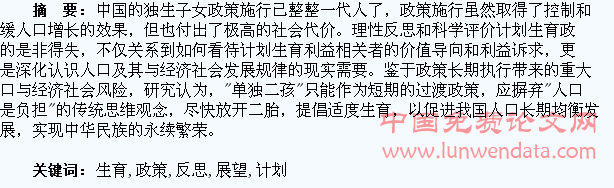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09-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1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inking from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XU 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China )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a whole generation, which produces not only the effect of controlling and slowing down population growth, but also a very high social cost. Scientific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gain and loss of the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not only involves how to tre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terest appeal of the birth controlling stakeholders, but also is a realistic need to deepen the cognition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iven the big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 which arises from longrunning policies, the paper insists that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can be only used as a short transition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pulationbeburden and let go two births as soon as possible, advocate moderate ferti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tion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e population problem; reflection;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prospect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意义非凡。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40多年来,在取得生育率下降、人口转变、减少人口增长等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未富先老”、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风险提醒着我们,该是系统反思和深度调整这一公共政策的时候了[2]。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社会各界从未停止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如何判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政策及评价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我们能否止步于“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前景是什么?本文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尝试厘清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希冀助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纷争与得失之辩
1.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理论纷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研究者类似经验交流的文章。当时,人口学尚未恢复重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界着重阐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实效性。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实施[3]。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等论题受到重视。并且,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规模的增大,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心理和人格发展等成长问题。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没有质疑,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尚在生成之中。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国内少数人口学者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的弊端,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提出“少生不是一切”,认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人口论”,也要重视“人手论”。中国需要一种在持续发展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大人口观”[4]。首次提出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与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认为不能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简单化为生育问题;在理论上批驳了“人口多”是“人口负担”的代名词、人口多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人口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等错误观点[5]。 进入新世纪,各种人口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首先是2000年“五普”数据的公布,1.22的总和生育率震惊了全社会,人口学界更是无法相信如此超低的生育水平。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8[6]。2010年“六普”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只有1.18,人口统计专家再次将其修正为1.5左右[7]。总和生育率历来被视为判断人口转变的核心参数,这正是人口学界争论不休的要害所在。近十年来,人口学家围绕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辩,直到最近几年才形成我国生育水平处于1.5~1.8之间的共识[8]。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统计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卫生及教育部门乃至学术团体在抽样方法和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彼此间测算的生育率差距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社会流动加剧,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和漏报,但是最近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9]。因为相比于普查,抽样调查同样存在瞒报和漏报现象,而且抽样规模越小、抽样随机性越差、调查组织越不规范,所得到的数据越不准确、越不靠谱。
除生育率焦点之争外,与其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也受到高度重视和热议,比如人口转变、人口安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均衡发展、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等方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国内3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在其推出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预测,其中部分结论和观点遭到质疑,比如认为“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左右,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10]。从这份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不难看出,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的智库们,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依然忧心忡忡。不过,人们似乎没有看到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10人,比“五普”3.44人减少0.34人,家庭小型化更加明显,家庭脆弱性进一步增强;总性别比虽然由“五普”的106.74下降为105.20,但新生儿性别比自1990年代初以来仍在高位运行,达到117.96;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6.6%,比“五普”时下降6.3个百分点,减少了27.5%,降幅之大令人吃惊;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3%,比“五普”时上升了2.9个百分点,增加了28.4%。并且,中国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快速老龄化、高龄化时期[11]。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2亿,占到总人口的14.9%; 8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2300万,空巢老人达到1亿[12]。可见,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及其衍生的养老保障、婚姻挤压等棘手问题[13]。无疑,少子女老龄化和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给我国人口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留下了长期隐患。
在诸多问题论争中,有关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问题备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核心理论依据就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对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取决于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特别要充分利用人力和人才资源。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所谓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多,而主要是缘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14]。另外,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历史回顾,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人们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研究者指出,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比较正常,和其他国家大体相当,即使不错批马老先生,也会多生所谓的3亿人[15]。况且,当时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和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因为党的指导路线发生了严重偏向,干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在最近几年的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讨论中,学术界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系统的有机组成,它们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并且将人口发展置于更大的自然、社会系统中考量,力求探寻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之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经过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两次人口转变,成为现代型人口国家。但我国是唯一通过严厉的人口控制实现第二次人口快速转变的国家,我们用了1/3世纪的时间便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16]。这种急刹车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换言之,我们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必将偿还因长期严格人口控制而导致的人口负债。
近些年来,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功绩论者与问题论者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功绩论者认为,计划生育使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节省了17万亿抚养费,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40年的人口红利[17]。有人口学者尖锐地指出,计划生育官员和部分专家夸大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即使将功劳全部归于独生子女政策,也不过少生了2亿多人;如果考虑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妇女普遍就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因素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只少生了1亿人左右[18~19]。实事求是地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减缓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相比,政策的效果显然大打折扣。关于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抚养比负担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基本前提,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多和低成本,与人口红利本身无关[20]。从而否认了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直接提供人口红利的说法。 问题论者认为,40多年计划生育特别是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问题,比如少子女老龄化加速、新生儿性别比长期高位失衡、过早的“未富先老”、1亿多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劳动力短缺且老化加剧、数百万“失独”家庭的产生,等等[21]。功绩论者反驳道,少子女老龄化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少子女有利于优生优育、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有利于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新生儿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中国“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导致的结果;“未富先老”尚无定论,我国目前人口负担仍然较轻,正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只要我们发展了经济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问题一定能够妥善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比多子女家庭风险大,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任何家庭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可能;我国劳动力绝对量仍然十分庞大,失业压力依然巨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失独现象与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对于失独家庭我们也很同情并给予积极的扶助。问题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独子难教、独木难支”,独子女的教育成本很高,独生子女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和品德上的不足,如果是两个孩子,则会降低抚养和教育成本,优化家庭结构,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叔伯舅姨姑等亲属,破坏了家庭自然人伦环境,撕裂了中国几千年的家文化[22]。农村“一孩半”政策是造成新生儿性别比长期失衡的重要推手[23]。新生儿性别比20多年高位失衡,意味着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将爆发数千万光棍危机,婚姻挤压造成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家庭和社会难以和谐发展。我国老龄化加速发展,将会严重拖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以来的多次民工荒表明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减少,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拐点开始显现[24]。各省市养老金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近年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延迟退休建议就是征兆,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我们将很可能步日本老龄化后尘,当社会严重老化时,国家创新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乏力。家庭少子女小型化空巢化、社会流动加速、传统孝道精神缺失,致使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遭到严重消解[25]。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深陷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困境,凭什么认为未来中国一定能解决好养老保障问题,国家对我国老龄化、高龄化后果估计和准备不足,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26]。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给我国人口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27]。计划生育人为催生了数以亿计的风险家庭,而且还在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系数,百万“失独”家庭就是这一风险的具体显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每年的“失独”家庭以7.6万速度递增[28]。“失独”父母内心痛苦,数百万“失独”家庭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还给家庭和社会制造了诸如贫困、妇孺身心健康受损、道德、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人口逆淘汰、国防等方面的风险[29]。
基于计划生育利弊得失及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的总体性判断,目前学术界存在“适度放宽”、“维持现状”、“适度从紧”三种观点,而持有“适度放宽”建议者较多。除以“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为代表之外,代表性的建议还有陈友华的“四步走”、曾毅的“二胎软着陆”、桂世勋的“双轨制”、王金营和赵贝宁的“放宽二胎,严控三胎”、翟振武的“不能踩急刹车”等调整方案[30]。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自觉、持续论辩以及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广泛传播,反思和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已经引起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可以视为这一努力的阶段性成果。
二、对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得失的价值评价
从上述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之辩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基于人口生育现象本身的学术思考,还是对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的批判反思,都会涉及一个更具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即关于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和评价者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背后的利益动机和行动逻辑问题。无疑,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国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随后改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就是要强制性控制人口的自然快速增长,人为减缓人口增速、减少人口增长直至实现人口负增长,以便形成一个适合我国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人口”,人口要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切政策措施都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看,如果对计划生育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那么在评价政策效果时会有意无意地偏袒政策或放大政策的正效应;反之,则很可能拒斥政策或放大政策的负效应。那么这种价值取向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人口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评价者究竟是将人口视为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如果将人口视为负担和包袱,或将人口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则必然积极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如果将人口视为正价值,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必然否定和力图改变现政策。进一步追问,哪些人更倾向于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哪些人更可能站在反对的立场?正如我们在批判唯心史观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仅仅考察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更应探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当然,毋庸讳言,在梳理学术界有关总和生育率之争、人口风险及政策得失之辩时,必须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对学术界具有强烈的导向和暗示作用,并且人口及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在政策制定和历次调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智库作用,我们仅从1980年《公开信》的发表、中央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决定的发布以及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出台中便可看出端倪。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呼吁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但是学者不是圣人,不仅存在个人利益,也存在个体的价值偏好,难以做到价值中立和学术坚守。而学术坚守是建立在责任良心和学术规范双重基础上的,如果偏执于道德说教或学术偏见一端,就会陷入道德自负或学术自负。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主义导向意味着价值中立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在一边倒的强势价值导向面前,反对者的声音弱小而难以传播和获得公众的认同。当然,大多数反对者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与当下支持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问题,而非短期的社会效益。 从计划生育实践和对政策的持续争论中我们隐约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言者之间的博弈,一种是对人口自身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第一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生育权利之争以及彼此间迂回曲折的博弈。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理性反思和大胆质疑仅仅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民众代言人主要包括人口学者在内的少数社会学者,还有个别海外学者及民间草根人士;而强势部门代言者则阵容强大,人口学家首当其冲,还有参与政策制订规划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其他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专家学者群体。民众代言人在和强势部门代言者初期理论交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和下风。因为政府通过长期舆论宣传让计划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普通百姓逐渐视之为自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倡导与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愿望较为接近,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为计划生育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心理认同基础。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遭到农民的抵制被迫做出部分调整,但总体上民众还是接受了现行的生育政策。与学术界两大代言者实力悬殊相比,民众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也是弱势一方,但是民众采取了“务实”的软硬兼施策略,或以种种方式拒交超生费用或靠拉关系走后门偷生、超生,利用政策漏洞和性别鉴定技术选择性生育。一句话,真正想生的家庭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生育目的。少数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在一票否决制的考核压力下,也采取了瞒报、漏报的投机主义手腕,甚至在社会抚养费诱惑面前干起了钓鱼执法的勾当。
第二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彼此间的矛盾显现使然,所谓实践出真知。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践在带来一定社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成本,并衍生了相关社会问题,这在客观上促使学术界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导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失衡迫使人口学界关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引发学术界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辩证思考,有关人口安全、人口红利、人口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概念应运而生。可见,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得益于对中国当下社会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提炼,而相关学科的成长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包括部分政府官员、“两会”代表委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法学专家、人文学者、企业家、海外学者及民间研究者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加入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反思和探讨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全社会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了解和理性思考,使人口研究跳出单学科的狭隘视角。不可否认,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广泛传播对于反思现行人口政策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对于社会问题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问题本身的特性。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认为,社会问题具有主客二重性特点,主观性表现在社会中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之中,他们明确肯定或否定某些东西为社会问题;客观性则表现在被评价的实际对象之中[31]。人口生育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亦是如此。人口与生育问题既反映了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的生育利益之争,折射出一定的主观建构色彩。其主要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导向、利益相关者对待人口生育问题的态度以及经济社会等环境变迁情况。
三、我们不能止步于“单独二孩”政策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饱受争议中施行了1/3世纪,迄今整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2013年底,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调整,这是对1980年《公开信》中承诺的“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一种回应,意义重大,值得肯定。社会各界备受鼓舞,最近一直热议此项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并对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事项作出了探讨和建议。然而,我们认为,仅仅实行“单独二孩”是不够的,严峻的人口形势客观上要求尽快放开二胎甚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此次政策调整的意义和价值。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一种城乡、地区和民族有别的多元化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我国在1980年秋至1984年春,将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调整为“晚一孩”政策,但是鉴于一孩政策在农村陷入窘境、难以为继的局面,中央于1984年发布7号文件,决定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即第一孩为女孩的隔几年经批准可以生第二胎,遂形成现行生育政策并稳定至今[32]。这期间,地方生育条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作出了符合生育二胎的具体规定,绝大多数省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作出规定,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即所谓“双独二孩”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无疑是近十几年来生育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据知情者透露,“单独二孩”政策历经十年酝酿,经过无数次的调研、讨论和测算。新政酝酿阶段,曾有多个方案进入决策层视野,折射出不同智库间的竞争、民间与官方的角力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衡。用人口学家的话说:“多少年坚决不让动、不许动,现在能迈出这一步不容易[33]。”据人口专家测算,此次政策的潜在受益家庭将达到1000万左右,真正受益人群是以往政策比较严格、生育率长期比较低的地区,比如城市地区、发达的省市;而西部一些省,特别是少数民族省份,政策的受益面会比较小。尽管此次政策受益面不大,只占到15~44岁有配偶的育龄夫妇的5.25%,但是政府适时调整生育政策,顺应了群众期盼,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生育愿望,有利于社会和谐[34]。
但是,必须指出,“单独二孩”政策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性。正如人口专家测算的那样,单独二孩受益面较小,而且近期符合条件且愿生二孩的家庭大约只有563.3万~755.6万[35]。我们知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换言之,最近几年符合条件且实际生育的“单独”家庭只是育龄夫妇家庭中很少的一部分,这对于解决我国少子女老龄化、降低新生儿性别比、减少家庭和社会风险以及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意义不大,可谓杯水车薪。况且再次催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在同辈群体中,育龄夫妇一方因为没有和独生子女结婚而无法获得生二孩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权威专家担心放开二胎会造成生育高峰和生育堆积,给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压力[36]。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相比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的长期风险而言,这种相对集中的生育压力只是暂时的、可控的,也是无法回避和必须承担的。鉴于我国20多年的低生育率已经累积了强大的人口负增长势能,目前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当我国人口提前达到峰值以后,将不可逆转地进入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轨道,陷入人口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此看来,即使按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建议,将我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现在也该采取不同于“单独二孩”的政策了。多次全国范围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大约在1.7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放开生二胎,也达不到1.8,更难达到人口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即2.1左右[37]。我国因性别比失衡、不孕不育等因素,可持续生育率需要保持在2.3左右。再者,我国已进入老龄化、高龄化加速期,意味着死亡率将不断提高,20多年低生育率早已消解了人口增长的惯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生育高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低生育水平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经过长时间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38]。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同样也收效甚微。令人惊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酒泉、承德、恩施、翼城四个地方实行的“二胎间隔”试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低于所在省份的其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无显著差异,干群关系融洽和睦。“二孩地区800万人的实践展示了执行二孩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和路径,而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的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生育水平绝对不是越低越好,低生育水平维持的时间绝对不是越长越好”[39],未来一段时间放开生育政策势在必行。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口风险的累积性、滞后性、隐秘性、不可逆性特点以及政策的时效性、两面性特点提醒着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生育政策的调控作用,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生育问题[40]。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41]。”在考虑生育政策时,我们起码要有30年的前瞻性,易言之,今天的生育政策必须和3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42]。现在,30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人口问题已经集中显现,我国人口及经济社会风险迫在眉睫,近期放开二胎,犹未晚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我们希望政府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精神,尽快放开二胎。
当下,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努力做起:第一,广泛宣传人口科学知识,淡化以前片面强调人口危害的做法,普及全面客观的人口知识,如实告诉人们长期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后果。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广泛的民意征询活动,创造条件让公众参与人口生育政策的讨论,集思广益,打破部分专家学者垄断话语权的现状,增进人口生育决策的民主性。第三,从控制人口转向提倡适度生育,淡化对人口数量的要求,充分意识到我国人口问题的潜在风险。“单独二孩”调整过渡期不宜过长,在实施两三年后发现没有达到预期的提高生育率、降低新生儿性别比、缓解老龄化等效果后,应迅速改为放开二胎政策,决策层应提前做好预案准备。第四,改革配套的管理制度,清理相关生育政策、法规、条例和奖惩办法,改变现行计生考评体系,减少直至废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第五,淡化以控制人口为目标的利益导向政策,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产生,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43]。第六,全面转变计生工作方式。“单独二孩”以及其后的“放开二胎”政策调整并不是说不要计划生育工作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仍然要坚持。随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组建,各级党委政府和卫计部门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在政策执行上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基层卫计部门的工作重心应从“优生”向“优育”转移,发挥其在卫生宣教、生殖健康、妇婴保健、避孕节育、家政养老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