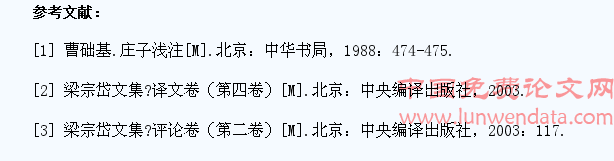电影《唐山大地震》人物悲喜情感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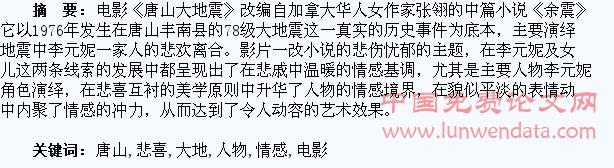
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电影是视觉的画面艺术,小说是语言想象艺术,这不同的媒介手段必然使两种艺术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小说里,惊心动魄的地震场景被一笔带过:“天咋就这么亮……突然间惊天动地一响……”只是通过作家对震前的场景描写去想象和体会这场可怕的灾难。电影里,这个情节是在数码技术与传统特效结合中完成的,而且有近5分钟的长度以造成震撼与惨烈的效果。小说中李元妮的女儿王小灯来加拿大已经十年,因家庭的缘故(实则是地震后心灵的分裂、失眠导致的神经过敏)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三次自杀未遂。作品开头有一段她与心理医生沃尔佛的对话,提到了梦中的窗,那推不开的最后一扇窗显然象征着主人公打不开的心灵之窗,灾后所受到的创痛,这也不是电影艺术所能直观再现的。当然,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也采取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比如其中以时间点为线索,采用了空间地点的转换――电影镜头闪回式来结构全文,为电影改编创造了条件。整体来看,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变动较大,且不说人物、故事情节的改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影片的情感基调比起小说来,更近暖色调,尤其是结尾。小说中女主人公最后回到了唐山,回到母亲居住的地方,远远地望见了出现在阳台上的老人,暗示心中的“结”被解开,电影则是王登经历汶川大地震后,与同做志愿者的弟弟相遇,两人一同回家见了母亲,并终于释怀了母亲当年的无奈选择,心中那扇封闭的“窗”真的打开了,大团圆结局。用作家的话说,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只想安安静静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揭示一块表面结了痂内里却烂成一片的伤疤。小说从始至终的主调是悲泣的、沉郁的,鲜有喜剧成分,而电影则是悲中有喜,以喜衬悲,角色的情感表现体现悲喜辩证原则的运用。
一、真悲无声,喜极而泣
悲喜互衬在影片里是贯穿始终的,大到幸与不幸、生与死、乐与苦、分与合、美满与缺失,小到细节的悲喜转换:失与得、心灵的分裂与弥合、疏离与亲近等。影片中有一情节:元妮在大地震后死了两个亲人――丈夫与女儿,剩下唯一的儿子――断了手臂的年幼的方达。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儿子是母亲唯一的寄托,更让母亲不舍的是,儿子的命是女儿替换来的。但这时,得知消息的奶奶与姑姑从山东老家济南来到了唐山,准备将这个孙子带走。他们怕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也怕万一儿媳妇再走一家,怠慢了孩子。奶奶痛失自己的儿子就更加心痛这个孙子,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元妮终被打动了,决定让奶奶和姑姑将孩子领走。元妮亲自送她们到汽车站,并将孩子送上车,口里不住地带着颤音对孩子说:“乖,听话。乖,听话!”当汽车渐行渐远的时候,元妮的心开始感到隐隐作痛,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一棵救命的稻草被人抽走一样,那种痛苦与无助如同心被抽空。只见汽车开动了,元妮呆呆地站在那里,欲哭无泪,欲罢不能,有万分痛苦状。这时,只见远处的汽车渐渐停了下来,出乎意外地孩子方达从汽车里下来了,孩子兴奋地伸开双臂(实际是一只手臂)呼喊着朝妈妈奔跑过来,元妮这时候也看到了孩子,她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扑向孩子,当她抱住孩子的那一刹那,电影的镜头渐渐离开了母子,从对元妮的特写变成远景的抽离了。当元妮号啕大哭的时候,我们作为观众被感动了,我们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对作为演员的徐帆来讲,对剧情的理解一开始并非如此。她认为当儿子与母亲分离的时候,是母亲痛苦到极致的时候,其表现就是号啕大哭。而作为电影导演的冯小刚是这样理解的:儿子与母亲分别,母亲是痛苦的,但他并不让女演员哭出来,当儿子从汽车上下来的时候,对于母亲来说,本该是高兴的事情,这时导演却让女演员号啕大哭。儿子突然回来,她哭了,哭得那么痛快,悲伤与喜悦的瞬间转换让她不由得哭了出来,则更突出她此刻的喜悦至极。
关于人的悲哀情感,中国古代的道家人物庄子就有过论述。“真”是什么?在庄子哲学中,“真”非现象而是本质,“真”也非外在而为内在。“真”与“伪”相对立,前者自然的、天然的、随性的;后者人为的、世俗的、礼仪的也。“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也就是说,悲到极致不是号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悲泣。如同老子说的:“大音无声、大象无形。”声音与形象的极致是不能用形式加以表现的,说得也是这个道理。同样,这种美学取向在16世纪法国的散文家蒙田那里也有精确的表述。他在《论悲哀》这篇散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埃及王皮山民尼图给波斯王干辟色大败和俘虏之后,看见他那被俘虏的女儿穿着婢女的服装汲水,他的朋友无不痛苦悲号,他却默不作声,双眼注视着地下;既而又看见他的儿子被拉上断头台,他依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可是一撇见他的奴仆在俘虏群中被驱逐,就马上乱敲自己的头,显出万分的哀痛来。”[2]11为什么会如此?蒙田在文中告诉我们,只有这最后的忧伤能用眼泪发泄出来,起初两个是超出表现的力量以上的。什么意思呢?蒙田在文中还举出一个画家的例子:画家画无辜美女的牺牲,他对在座的每个人根据与牺牲者关系的深浅来表现他们的哀感,但当他画到死者的父亲时,已经用尽他最后的法宝,只画他掩着脸,仿佛没有什么形态能够表示这哀感的程度似的。因此,蒙田说:“真的,悲哀的效力,到了极点,必定使我们的灵魂仓皇失措,行动不得自由。当我们骤然得到一个噩耗的警告时,我们感到周身麻木,瘫软以及举动都被束缚似的,直至我们的灵魂融作眼泪与恸哭之后,才仿佛把自己排解及释放,觉得轻松自在:直至声音从悲哀中冲出一条路。”[2]12蒙田借助于古罗马作家塞内加的话“小哀喋喋,大哀默默”。在这里,蒙田不仅说到悲哀的极致使人惊慌失措,就是意外的惊喜也同样如此,有因狂喜而丧命的,有陷入爱情的热烈而颓唐与憔悴的。在冯小刚的影片《一九四二》里同样有一个情节:徐帆饰演的角色因饥饿不得不卖掉年幼的孩子,徐帆觉得这样痛苦的事情一定应该是号啕大哭的。冯小刚对徐帆喊道:“我不需要你这样廉价的表演。”导演深知饥饿中的人们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可以用道德的评判来审视事物一样,人因饥饿而麻木不仁,亲情丧失,失去人的本性而变成兽性的疯狂可能更显常态化,也更能震撼观众的神经。 二、平静是内力的凝聚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结尾,母亲误以为阴阳两隔的女儿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潸然泪下的场景同样令人动容。因姐弟在汶川地震偶遇,姐姐看到汶川地震中母亲为救女儿,果断决定锯掉女儿的小腿,以保全她的生命,但母亲那种痛切心扉的悲号留在了王登的记忆里。她豁然领悟到当年自己母亲的无奈之举,心中那扇封闭的“窗”慢慢地开启。弟弟把姐姐领回了家见母亲。当姐姐走到院子里,母亲正在给孩子们包饺子。她颤抖的手勉强地捏着饺子皮,难掩内心的激动,头也不抬地说:“进屋吧,先进屋。”姐姐进到屋里。她慢慢地环顾四周陌生的一切,看到了墙壁上父亲与自己的遗照。照片下的桌子上是一盆清水泡着的新鲜西红柿。这一切唤起了方登儿时的记忆。这时弟弟上前从墙上摘下姐姐的遗照。母亲缓缓地从外边走进来:“这些年你都去了哪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说着,拉长了声调“我还以为你和你爸在一起呢?”颤抖的声音哭诉着,手扶床栏杆跪了下去:“妈给你道歉,对不起了。”随后号啕大哭起来。姐姐止不住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赶紧上前搀住母亲。母亲声音哽咽。母女俩抱头痛哭起来。
这个情节恐怕是本片最感人的镜头之一了。得知女儿活在世上,32年后母女见面怎样开场,的确是值得导演思虑的问题。影片中设计的母亲包饺子的动作,不敢抬头看女儿,手在不停地抖动,这表面的平静实则内涵着巨大的情感冲击。母亲突然下跪的情节,这泪水不仅是对她选择了救儿子而舍女儿的愧疚,更是一种多年压抑的情感释放!一直以为已经在地震中死去的女儿现在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这种失而复得,突如其来的喜悦最易使人惊慌失措,此时的喜悦已化成川流不息的眼泪,而女儿对母亲32年来的怨恨也随着这泪水而流逝,这个家庭32年的怨恨枷锁终被解开。
中国现代诗学家梁宗岱在其散文《论崇高》一文中引述了两段外国诗人及思想家的日记,一段为19世纪法国诗人格连的:“昨天,西风狂暴地吹着。我看见那汹涌的海了。可是这凌乱,无论怎样崇高,在我看来,也比不上那平静而且蔚蓝的大海底景象。但是为什么要说这比不上那呢?谁能够测量这两个崇高的境界,并且说‘前者比不上后者’呢?让我们只说‘我的灵魂爱宁静比波动多’好了。”[3]另一段是瑞士思想家亚美尔的日记:“静呵,你多可怕!可怕得像那晴朗的大海让我们底眼光没入它那不可测的深渊一样;你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看见许多使人晕眩的深处,许多不可熄灭的欲望,以及痛楚和悔恨底宝藏。狂风吹起来吧,它们至少会把那蕴藏着无数可怕的秘密的水面摇动。热情吹起来吧,它们吹起灵魂波浪同时也会把那些无底的深渊遮掩。”[3]
这也适用于情感表现之力了。貌似平静的海面实则有无限深渊潜藏,而汹涌的巨浪将可怕的一切诉诸眼前,静穆比起咆哮更能令人心生敬畏之感,因之积聚着巨大的内力。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张静初饰演的王登,本人感觉把握较好。原小说中就是以王小灯为主要线索,展开人物震后坎坷命运以及心灵分裂,地震中因母亲无奈放弃,心中始终怨恨纠结,又遭到养父的猥亵以及婚姻的不幸等,出国后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患得患失,其形象始终是压抑、沉重的。影片中虽然对原小说故事情节有改编,比如王登的养父母,从普通的职员(母亲是英语教师,父亲则是工厂的处级干部)改成了军人,而电影中的养父陈德清是一位正派、慈爱而多情的军人,但因继母的敏感与多疑,使王登还是谨小慎微地与养父保持着情感上的距离,内心深处关于生母的记忆以及怨恨始终没有化解,带着这样的伤痛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可想而知她会怎样的小心翼翼!影片中军人养父的扮演者陈道明的表演可圈可点,相当精彩。有这样一个情节:考上大学的王登已经有两个暑假没有回家看养父母了,陈德清来到学校看望女儿。父亲给女儿带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女儿问:“我妈身体好吗?”此时镜头拍的是被汗水湿透的陈德清的后背,只见他忙着往外掏东西,听到女儿的问话,不由地停止了,慢慢地抬起头,平淡地说了一句:“不太好。”“什么叫不太好?”陈的语气仍然很平静:“住院了。”“我妈怎么了?”父亲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湿毛巾:“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只是说你两个暑假没回家了,让我看看你就行了。”“我妈为什么住院啊?”陈抬头惊异地看着女儿。“我妈到底怎么了?”陈紧皱眉头,看了看窗外,然后用湿毛巾捂着脸,低声说:“你还是回家看看你妈吧。”平静的外表下深蕴着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令人动容!如果此刻演员大声地斥责女儿,为什么有两个假期没有回家,或如实地告诉女儿妈妈得了绝症,恐怕那种深沉感人的力量会大打折扣的。
《唐山大地震》就情感美学而言并非登峰造极之作,从某种角度讲演员的表演还有许多痕迹,尤其是地震发生之时,人们只顾逃生是来不及哀号与谩骂的。本文仅通过影片的几个细节来说明,真正打动人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力所能达到的,恰好相反,一定是内力支撑下无形的“表现之表现”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因此西方思想家提出的“我的灵魂爱宁静比波动多”的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