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沈从文文学作品外译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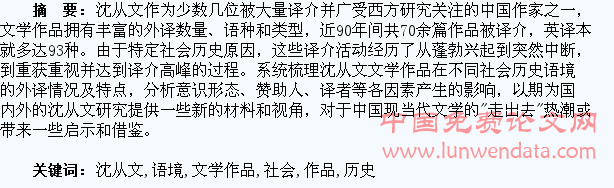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76-007
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多产作家,其丰富的题材、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广获国内外赞誉。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进入全球研究的视野。而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经典与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为外文,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译介新作品的同时,对经典文学资源的创新利用也值得重视,诸如西方汉学一直关注的现代作家仍有不小的译介与研究空间。沈从文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是极少数被大量译介的中国作家之一,对其文学作品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外译情况及特点系统分析,或许可对现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有所借鉴。
沈从文踏入文坛不久,作品译介就已出现。1926年他的戏剧《母亲》首次被译为日文,发表于四月的《北京周报》。据其家书记载,同时也已有多篇小说英文本发表。(1)而在现在可考的沈从文作品英、法译本分别始于1936年与1932年,德语、瑞典等小语种则主要始于80年代。体裁主要为小说(45篇),也含散文、文论和书信等,共计70余篇/部作品,现存英译本93种,德语译本20余种,法、瑞、日译本各十余篇,此外意大利、俄罗斯、荷兰、挪威等多国也有相应译作发表出版。各语种译者总计近百人,涉及东西方汉学家及在华记者、专业译者、华人学者和作家等。这些外译作品发表途径主要为五类:国内外期刊,如《天下》月刊、《中国文学》、《袖珍汉学》;外译中国文学选集,如《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沈从文作品翻译选集,如《中国土地》、《不完美的天堂》;外译单行本,如《边城》、《沈从文家书》等; 文学翻译网站,如“纸托邦”(paper republic)。
自20世纪30年代译本正式出现起,至今已逾90年,按照历史背景可分为五个阶段,以英译为例,各时期译介数量可见下表(不含重复发表和再版)。而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这些译介活动也各有特点。
一、1936―1949:民族危机与中外知识分子译介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先后遭遇抗战与内战,面对国家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变革救国意识不断增强,各类思潮争鸣,名家名作频现,这也是沈从文创作最蓬勃的时期。国际上,随着二战愈演愈烈,作为东方战场的中国引起西方关注,不少记者作家来华采访报道,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对于一些知名作家,译文也紧随热销作品而生。沈从文作品起初由国内知识分子译为英、法语,随后英美译入大增,篇目以最知名的乡土小说为主,15年间共产生22篇英译、5篇法译作品。而战争也未影响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十余年间3本日语沈从文译文集面世。
就译出而言,《天下》月刊发表英译沈从文小说最多。最受好评的《边城》出版两年内就由项美丽与邵洵美译为“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翠翠),连载于《天下》1936年1月至4月号,是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作品英译;此外还有李宜燮翻译的《萧萧》(1938)与佚名(杨刚)翻译的《乡城》(1940)。《天下》也成为沈从文作品首度译出的媒介。而法语译者张天亚(Tchang Tien-ya音)三篇小说译文也发表于介绍国际时政、外交、文化内容的国内法文刊物《北京政闻报》(La Politique de Pekin)。1932年,该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法文《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1]149
西方译入方面,译文多收入英译中国文学选集,另有英、日四部沈从文选集。众多译本主要缘于抗战期间西方希望更多了解变革中的中国文学与社会,而相关外文资料极大缺乏,译介需求强烈。1936年,沈从文的诗《颂》首次英译收录于艾克敦 ( Harold Acton) 和陈世骧编纂的《中国现代诗集》。而埃德加?斯诺所编的《活的中国》是其小说首次在国外刊出,收录短篇小说《柏子》,作者简介中将其誉为中国的大仲马。1944年,王际真编译的《现代中国小说》收录《夜》,是沈从文小说首度面向西方学术界发表。而当时白英(Robert Payne)英译贡献最大:1946年他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袁家骅合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收录《灯》和《黑夜》,导言中用大段篇幅介绍沈从文,称之为中国的高尔基; 1947年他与学生金?合译《中国土地》在英出版,收录14篇小说,是对沈从文空前的专门大规模译介,该书于1982年再版,影响深远,之后几十年间西方沈从文研究中常引其译文作为分析材料。而在日本,一批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青年学者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社”,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其中就包括散见于期刊的多篇沈从文作品。此外,1938松枝茂夫将沈从文的8篇小说译为日语,并以《边城》为题出版;40年代另有两部沈从文日语选集《湖南的士兵》和《沈从文短篇集》在日出版,引起了日本学者广泛关注。[2]
至于译者,项美丽、白英、斯诺均为抗战前后来华的西方记者作家,翻译出于介绍中国现状的热情。此阶段英译形式主要为中外译者合作,22篇中仅4篇为中国译者所译,其余项美丽与邵洵美、金?与白英等均为合译,由中国译者初译,再由西方译者修改润色。这既显示了当时中西方学者合作交流密切,当然也可能因沈从文多用俗语方言,对西方译者是极大的翻译障碍。与英译不同,基于日本汉学的深厚渊源,日语译本则分别由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大岛觉、冈本隆三独立完成。 翻译策略方面,早期译作多面向普通西方读者,重视内容主题,以归化意译为主,翻译中常见简化删节乃至改写。项美丽在前言中阐明其翻译理念,解释为何更改标题且不作单独注解。而斯诺的前言也指出此书翻译并非为汉学家服务,而是要让普通外国读者看懂进而了解中国,因此“这些小说并非‘直译’”而是“努力传达作品的精神”,“有时无法保留需长篇注解才可说明的双关或典故隐语,以免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国‘离奇’的成见”[3]。他彻底改写了《柏子》结尾,让原文中满足归去的柏子意识到“这个世界哪里不对”,从蒙昧走向觉醒,体现当时社会语境下中国人民的抗争觉悟[4]。另外多位译者都提到中国小说往往冗长松散、辞藻繁复,不符合西方阅读习惯。为求行文简洁紧凑,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删改原文。白英的译本就多有细节及心理描写被简化合并或删去,中国特色的典故事物则常被西方相近意象代替或略过。
这些翻译活动赞助人来源不一,但尚无政党和官方介入。《天下》的经费来自中山文化教育馆,负责人孙科明确将之定位为民间学术组织,目标即弘扬中华文化。[1]15-17译入则多为西方在华人士发起,以介绍中国文学和社会为目的,由英美出版社支持。任职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及日本汉学家们则由高校研究所赞助,编译选集作为中国文学教研书目。正因这些译介由知识分子主导,尚未受官方意识形态束缚,具体篇目选择多出于译者作家的个人喜好评判。邵洵美曾撰文称《边城》是“中国近代文学里第一篇纯粹的故事”,因此要向外国人介绍这部成功之作[5]。
总之,该时期译介由国内外知识分子主导,译出与译入并存,尚无官方赞助。翻译形式以中外译者合作较多,由于译作为向国外大众读者宣传中国文化,早期译者的篇目选择多出于个人偏好,翻译中更注重故事情节性,常有简化删改。无论如何,这十多年间蓬勃发展的译介活动成为沈从文作品走向域外的第一步。
二、1950―1959:意识形态冰封与译介断层
相对于三、四十年代的众多译本,五十年代沈从文作品译介骤然中断,再无一部作品外译。这一特殊现象的根源是四十年代末沈从文被国内官方文艺界定性为“反动作家”,从此遭受了近三十年的冰封。
1948年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斥反动文艺》,将反动文艺分为五色,沈从文则作为桃红色作家代表首先被批判:他的《摘星录》、《看虹录》被批为“文字上的裸体画、春宫图”,而这些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对这类反动文艺作品“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并号召大众“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同期刊登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认为其对熊希龄居所的描写“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也是最反动的文艺。”(2)虽然在京派与海派之争中沈从文也常受抨击,但大多针对文学作品本身,这两篇文章却是对沈从文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1949年自杀未遂后,他终于放弃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
沈从文创作停止后所受攻击并未减弱,相反国内文学史教材也开始了对他的长期批判或漠视,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等。这些受“左派”影响、注重阶级分析的教材以马列思想为纲,以对作家本人立场的讨伐取代应有的文学批评,一致将沈从文定性为反动作家,作品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6]此后国内其他文学史中,沈从文要么作为反动典型,要么彻底消失。雪上加霜的是,1953年曾出版《边城》、《长河》等多部作品的上海开明书店通知沈从文,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待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沈从文在该店的一切著作纸型也被完全销毁。(3)
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译介可见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对外宣传,1951年《中国文学》创刊,由外文局负责编译,1953年8月成立季刊编辑部,全国文协推定的编委会负责选题。1959 年起刊物向外办、作协、文委汇报工作,听从三方面领导指示。[7]在这样的官方赞助统管下,大量英译现代文学作品发表,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阿Q正传》(1953)、《鲁迅短篇小说选》(1954)、《鲁迅选集》1至4卷(1956―1961),及郭沫若的《屈原》(1953)、廖鸿英所译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也分别由许孟雄、沙博理和叶君健翻译。众多英译书目之中唯不见沈从文的作品。
对沈从文的长期封禁不仅出现在大陆,台湾亦是如此。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期,因拒随国民政府南下、且发文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沈从文被列入禁书名单。当然他并非唯一被禁的大陆作家,“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还有鲁迅……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4)
这一时期,大陆和台湾官方均将沈从文在各种“正统”文学史上贬低或是抹去痕迹,对其作品下达禁令、清理乃至销毁印版。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国内文学作品译介主要为官方外宣服务,将一个“反动作家”译出自然无从谈起。至于西方,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差异使得多国对中国展开经济文化封锁,而沈从文大量作品被毁加之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消失也令新一代西方学者无从了解,亦难获取中文作品,终究造成了译入与译出同时断层的局面。
三、1960―1979:文艺“小阳春”与海外研究重促译入
60年代起,中断的沈从文作品译介终于继续。国内由戴乃迭翻译的《边城》发表于1962年的《中国文学》杂志,而在西方,因夏志清等华人学者力捧,沈从文引起了欧美学界重视,英法译本也随学术研究的需要和热情再度兴起。
该时期唯一译出的作品《边城》得以面世要归因于短暂缓和的政治气氛。1961年6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 1962年定稿通过 “文艺八条”,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令遭遇反右的知识分子有了“怀柔”的机会。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中也提及这段“小阳春”的政治气候,忆起“文艺座谈会”小组会上,有发言者称赞沈从文,主持者也表态支持他继续创作。[8]此外,三年经济困难也使政治运动暂缓,气氛相对放宽。这一政治背景下,《中国文学》除指定作品外,也陆续发表了译者自己提供的稿件。《边城》由戴乃迭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1962年第10、11期,是20多年内唯一由中国官方赞助的沈从文作品英译。但“小阳春”好景不长。不仅沈从文再次被打倒,1968年杨宪益夫妇也因被怀疑为特务入狱。自“文革”初始,《中国文学》对于现代和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就已停止,全部改为翻译关于“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作品[9]。 相对国内译出的昙花一现,西方译入稳步发展,共10篇作品英译,1篇法译。不乏首获英译的篇目。这一趋势主要归功于夏志清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对沈从文推崇备至,认为 “沈从文的田园气息,从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10]该书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使沈从文及其作品突破了国内文学界的刻意封锁,终获应有的重视。此后,聂华苓的《沈从文传》于1972年在美出版,是第一部介绍沈从文生平和创作的英文专著。自此西方学者的“沈学”研究日渐兴起。金介甫、威廉?麦克唐纳德(William L.MacDonald)等多位学者均将沈从文作为博士研究课题[11]。海外研究也进一步带动了作品译入,如麦克唐纳德还翻译了《一个大王》节选和《静》,而其他作品也均由海外学者英译,多收录于新编纂的六部中国文学英文选集,如翟氏父子的《中国文学宝库》选译了《龙朱》,夏志清与叶维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则收录《静》和《白日》。1970年,法国汉学家赫美丽( Martine Vallette-Hémery ) 翻译的《新与旧》(Autres temps,autres moeurs)收录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中文小说1918―1942》 和《十三篇中国小说1918―1949》两本法语文集。[12]28
赞助人方面,《边城》发表于官方杂志《中国文学》,译者也受聘外文局,彼时恰逢意识形态管控放松,湘西乡村的故事也未触及阶级斗争的禁区,小说才得以首次由官方赞助译出,不过也仅是特例。纵观这20年间的西方译入,学者发起的译介活动多由以欧美高校为主的学术界赞助,出版机构均为大学或教育类出版社,因此这类译本也呈现更强的学术性特点。
从译者主体及其翻译策略来看,戴乃迭是专业译者,但有别于白英、斯诺等西方译者,她在中国生活多年,对历史文化了解更深。她不赞同过分创造性翻译,倾向于灵活性较小的直译方式,对于特定文化词汇也多作脚注或文中解释,尽量忠实原文。[13]而西方译者如夏志清、叶维廉多任教于美国知名高校,身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其译文多用作高校汉学教材,服务于师生的教学科研。针对专业读者,文本选择既关注作品的故事性,也强调文学性和代表性,翻译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的面貌与特色,尊重原作,不会多作删改。
纵观六、七十年代的译介活动,除特定时期官方赞助戴乃迭翻译《边城》外,其余译文均为西方译入,主要由西方学者发起,多为文学选集篇目,面向学术界。相较50年代前的译者,他们的翻译力求贴近源语与源文化,相对忠实。十多年的译介断层后,随着全新译本陆续发表,沈从文开始真正进入西方学术研究视野。
四、1980―1999:“沈从文热”与研究译介高峰
自80年代初,沈从文作品在西方进一步被接受,数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金介甫、夏志清、马汉茂及马悦然等海外学者大量将其作品译介。除英译外,法、德、瑞、意等语种译本纷纷涌现。随之而来的“沈从文热”也催生更多译本,相关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实施,政治文化环境更为宽松,打倒的名家得以平反,沈从文作品也终获解禁。海外热潮令他重受国内学界重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正式认可,官方开始大力支持英语、法语译出。这20年是译作产出最多的时期,仅英译就有54篇新译本面世,占其文学作品英译总数的58%,特别是19篇都为未曾译介之作。其他语种方面主要以汉学家及华人学者译入为主,多见于选集与期刊。
八、九十年代,大陆的沈从文作品译出均通过《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发表,共10篇小说和9篇散文。“熊猫丛书”的《湘西散记》和《边城及其他故事集》是大陆首次出版的英译沈从文作品集。法译《边城》与《菜园》、《知识》也分别刊于1980与1989年的《中国文学》法语版。同时,港台的沈从文译出也悄然出现。1989年香港的《译丛》发表金介甫翻译的《在昆明的时候》;《神州展望》1997年发表杂文《中国人的病》英译;1997年台湾的《淡江评论》刊登《福生》英译。与大陆官方赞助译出不同,这三份刊物分别依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台湾淡江大学,均属科研机构期刊,译出针对学术研究。
西方译入方面,80年代仍以英译文学选集篇目为主。夏志清等主编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tories & Novellas:1919―1949)是迄今收录沈从文作品最多的中国文学选集,5篇小说英译的数量仅次于鲁迅,足以突显学者们对沈从文的重视。《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也收录了欧阳祯翻译的《萧萧》。90年代,金介甫组织翻译了《不完美的天堂》,收录沈从文26篇作品,该书篇目选择注重文学性和题材多样性,特别是未译过的文章。除了乡土小说,也纳入关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都市小说,如首获英译的《八骏图》与曾被认为佚失的《看虹录》,最后还收入戏剧和民歌,而这些题材和文类之前一直被忽视。有别于其他沈从文选集,全书依主题分为八章,每篇译文前加入分析导读,供学习研究者和大众读者参考。而沈从文的文论也首度英译:马汉茂和金介甫编纂的《现代中国作家:自画像》收录两位华人教授合译的《小说与社会》;丹顿的英译文论集《现代中国文学思想》(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收录了金介甫翻译的《一般或特殊?》。其他语种方面,自1980马汉茂等翻译《我的教育》开始,德语译本大批面世,共20余篇,含五部沈从文散文、小说和自传文集。在法国,汉学家何碧玉于90年代致力翻译出版了《边城》、《从文自传》,另译有数篇小说散文收录于法语中国文学选集中。而在瑞典,马悦然等汉学家对沈从文也甚为推崇,共有《边城》、《静与动》、《孤独与水》三部译文集出版。[12]29
译者中成果最丰富的要数戴乃迭和金介甫: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17篇作品,登载于《中国文学》多期,“熊猫丛书”的两本也均为她独立翻译;而国外译文中金介甫数量近半(14篇)。其他主要的港台和西方译者如许芥昱、马汉茂、马悦然等均为学者,与六、七十年代相似,学术身份也决定其翻译策略秉承学界尊重原作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译文中“厚译”策略常被采用,附加大量补充注解与介绍之类“副文本”,尤以金介甫的译本为代表。 至于赞助人,八、九十年代大陆的沈从文作品译出均由官方支持,1980年起杨宪益出任《中国文学》主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翻译也享有较高自由度。但官方背景之下,选译篇目仍为乡土小说和散文,未涉及曾受批判的敏感作品。因《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定位为外宣,面向大众读者,具体翻译过程中,对于一些政治词汇、较露骨的情爱描写或不雅的方言俗语,也常有简化或少量删减。西方译入则延续了70年代的动态,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学术界,港台译出也是类似。赞助人仍是关注汉学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出版方也多为大学和学术出版社,因此译介篇目选择更多考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特色,注重对原文充分翻译。
八、九十年代,沈从文作品的外译主体延续了六、七十年代的特点,由专业译者与海外学者构成。但在“沈从文热”催化下译介数量激增,《中国文学》大量刊登其作品译文并结集成册,港台的译出初现,而金介甫、马汉茂、何碧玉等汉学家也继续推动翻译。篇目选择更多关注从未译介的小说和散文、文论等多种体裁。在大陆官方赞助、港台与西方学界支持下,译介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五、2000年至今:文学“走出去”与译介新趋势
2000年后,由于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现当代文学译介持续走热,但英译关注点更多转向新兴的当代作家,已有众多译本的经典作品则多以再版形式出现,新译较少,沈从文作品译介数量也相应锐减,新作仅6篇,但也展现出新时期的译介特点。而其他译本多为金介甫及戴乃迭译文再版。而相对英译减少,新世纪其他语种的译入则有所增加,各国汉学家对于沈从文的研究仍在继续。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新译本是金介甫英译的《边城》(2009)。不同于此前三个译本,金介甫凭借多年研究积淀,延续其“厚译”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民俗作了详尽解释,文末附加注解多达四十余条,可谓《边城》最充分的译本。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译介忽略的沈从文书信先后由李翊云和刘欣英译,分别由美国《公共空间》杂志(A Public Space) 和译林出版社推出。李翊云还参与了旧金山翻译艺术中心“两种声音”读书会,向美国读者介绍沈从文,并当场朗读家书译文。书信是了解作者生平经历的最直接材料,英文版的问世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国外“沈学”研究大有裨益。此外,《美丽湘西》(Beautiful Xiangxi)在美出版,文字由马克?基多(Mark Kitto)翻译,配合湘西摄影作品。作为一本摄影配文画册,文本按主题分为“长河”、“女人”等八节,节选自不同篇目,而非某一部作品,这在所有译本中也是特例。祁寿华在美编译出版的《当代中国闪小说》收录微形小说《代狗》。而最新译作是2015年坎南?莫尔斯(Canann Morse)重译的《夫妇》,作为“纸托邦”网站11月短读项目,提供免费全文阅读。其他译本均为国内和香港再版,有些以双语对照形式作为英语学习读物,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金介甫译文的双语《沈从文短篇小说选》,译林出版社的双语译林选取了戴乃迭的《边城》和《湘西散记》译本。
至于其他语种,新世纪日本汉学界的“沈学”研究不断发展,已出版四部沈从文译文集:城谷武男的《瞥见沈从文翻译集》(2004),小岛久代则翻译了《湘行散记》(2008)、《沈从文小说选》(2013),山田多佳子翻译了部分家书《鄂行书简》(2010),此外,沈从文研究专刊《湘西》自 1999 年创刊至 2008年终刊,共10期,专门登载关于沈从文相关的论文、资料与译作等[14],是沈从文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宝贵平台。在法国,2012年又出版了文集《湘西散记及其他小说》。而在俄罗斯,汉学研究此前多聚焦鲁迅、巴金、茅盾等作家,近年来开始关注沈从文,2010年已有以沈从文作品为题的副博士论文, 2013年《边城》被译为俄语,收录于同名的中国现代作家文选。
时间上,新译作和再版多出现于2008年后,与“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一致。2002年文化“走出去”概念就被提出,但随着2006年“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与2007年十七大报告推出,该战略才再获强调,中国文学译出的热潮兴起,主要由官方赞助推动。《沈从文家书》及其他再版译作均由译林、外文社等主流出版社承担。同时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纸托邦”网站最初作为一个翻译民间组织由中国文学爱好者于2007年建立,之后逐步与官方合作并已成为中国文学译出重要平台,《人民文学》的英文《路灯》杂志(Pathlight)便是合作产物。基于外宣和文化传播目的,这些译本的目标受众也从学术研究者更多转向西方大众读者。
总体而言,新世纪沈从文作品译介题材和形式呈现新的趋势,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首先,译者身份多样:既有金介甫、城谷武男、小岛久代这样致力沈从文研究译介的汉学家,也有海外华人作家李翊云、英国作家马克?基多,更有数位拥有中西方教育背景的新生代译者,如刘欣和坎南?莫尔斯,这些活跃于译坛的中青年译者肩负起了对中国文学译介的传承。其次,题材多样,沈从文的书信和微形小说都是首次外译。再次,发表形式多样:除传统的文集,摄影集用译文配合湘西风情照片,图文结合进行文化宣传,国内人文地理书籍外译或可借鉴。而李翊云参加读书会,面对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作家作品,也是有益的译介宣传活动。同时,这些译介活动也更善用网络媒介:《夫妇》参与了网站短读项目,李翊云所译家书及读书音频也同期发表于杂志网站。这些网络平台的在线阅读比传统纸媒更方便广大读者获取,有利于扩大影响力,更有效地推广中国文学。
结 语
近90多年间,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外译经历了从蓬勃兴起到中断再到重获重视并达到译介高峰的过程,众多数量、语种和类型的译本也随之产生,至今仍在继续。总体上,有别于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译介趋势,因特定历史背景,其作品英文译入数量远大于译出,海外发表的译本数为国内的两倍多。译介赞助人也有明显转变,由知识分子群体发起到海外学术机构为主导再到中国官方推动。译介主体以西方译者和海外华人占绝大多数,学者数量最多,专业译者和作家其次,不过近年也出现了译者年轻化、多元化的趋势。 众多中国作家中,沈从文之所以能在西方学界获得了较广的影响,与大量译介可谓相辅相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而言, “走出去”热潮下,特别是莫言获诺贝尔奖后,中文书籍被不断外译,在西方的接受和影响却不尽人意,而研究沈从文这样名家的成功译介过程,可以发现,相较于当代通俗新作,文学经典经过时间的检验,重译或翻译之前未译的这些作品仍然很有必要,特别是俄语、西语等小语种方面译介空间仍然很大,国家的出版项目或可提供相应支持。此外,对于中国文学,目前最主要的读者群仍是西方学术界,因而更多举办汉学相关国际学术活动,以研究促译介是扩大影响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助于发掘培养新的译者,充分发挥西方汉学研究者的译介作用。而针对大众读者,在新时期也需要创新的发表与宣传形式,不局限于传统书籍期刊,文字与读图、声像都可以结合,而各类网站甚至社交媒体也是宣传推广的良好手段。这些经验启示或许能对中国文学作品与作家更好更远地“走出去”有所助益。
注释:
(1)目前各类沈从文译介研究资料均认为其作品英译始于上世纪30年代,而事实上1927年9月2日沈从文致沈云麓的信中就提到:“听士隽(张采真)从汉口来信,说,我的好多小说,被人译到汉口中央英文报上,是个姓施人译的,士隽又为我作了篇英文的略传”(《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4-5页)。高艳红在《孙伏园的副刊编辑思想研究》文(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中也证实了此英文报的存在:“ 《中央日报》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机关报,1927 年 3 月 22 日在汉口创刊……同时刊出中文和英文版。英文版日出对开一张,由林语堂、沈雁冰、杨贤江等编辑,其内容取自中文版。”张采真正是该报编辑。但由于战乱,英文版《中央日报》未被保存下来,这些译本已无法获得。
(2)《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1948,(3)。
(3)见 1954年1月 沈从文复沈云麓、复道愚书信。《沈从文全集》第19卷 376-379。
(4)廖信忠:《走过禁歌与禁书的年代――禁书篇》,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82148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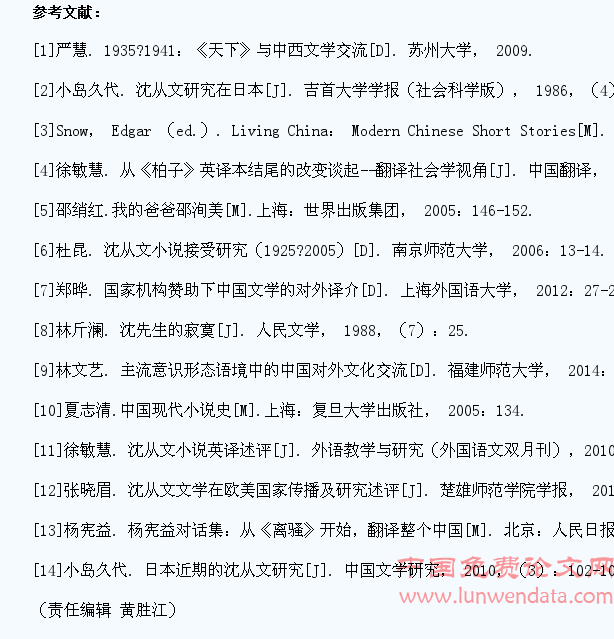
- 上一篇:势:一个实用主义社会学概念
- 下一篇: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