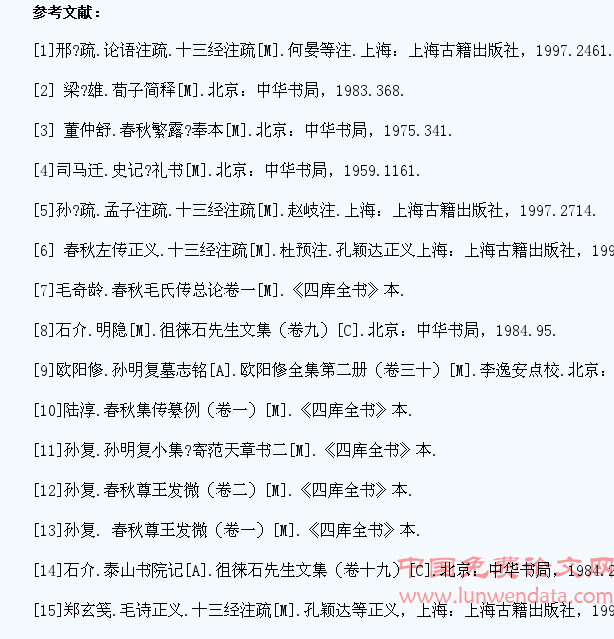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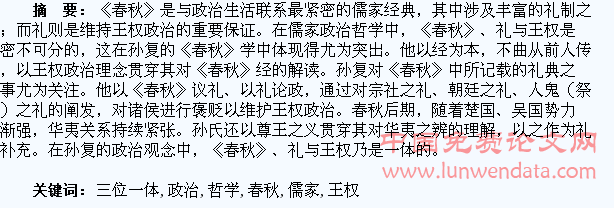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48-08
一、《春秋》、礼、王权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王权与礼典问题总是紧密相联系。统治者通过根据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况而制定或损益礼制、典章规范社会风气,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周公为了维护周天子的王权,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制定了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阶层构成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制度。与此同时,他对流传下来的古代礼仪及习俗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改造,使之成为以维护天子权威和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周公的制礼活动,又直接影响了孔子及其后学的礼治思想。孔子推崇周公,将礼制思想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他在探讨为政之道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荀子继承了孔子重礼的观念,对礼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礼者,政之轨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2]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2](371)荀子处于战国时代的末期,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即将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的需要。随着短暂的秦王朝的灭亡,汉初统治者开始休养生息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与此同时,儒家礼典在维护巩固王权政治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逐渐为学者和统治者所认识。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3]汉武帝曾经下诏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途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4]可以说,自汉武帝时始,儒家的礼制典章才真正与国家政权和王权政治切实结合在一起,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支撑。
关于礼制,儒家有专门的经书。因此,儒者议礼并不一定依赖《春秋》。但是,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无疑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大一统体制下的王权联系最为密切的经典。关于《春秋》与王权的关系,孟子最早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天子之事也。”[5]孟子的说法为后儒所接受和发挥。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3](198)董仲舒也认为《春秋》为孔子制作,通过对史籍的梳理进行是非评断,以确定包含王公、万民、贤才在内的政治秩序。他在另一处说:“《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3](135)董仲舒已经开始通过对《春秋》中礼的分析来阐发王权大一统思想。杜预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6]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指出:“(仲尼)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修《春秋》也。”[6](1705)清儒毛奇龄在其《春秋传》中说:“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7]毛氏并不否认《春秋》中有褒贬,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可见,对礼的重视在历代《春秋》学者中并不乏其人。《春秋》经传中涉及了相当丰富的礼制问题,如祭祀、继承、朝聘、盟会等,范围相当之广。以《春秋》议礼、进而以礼议政成为学者表达自身政治观念的重要途径。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特色。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一特色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孙复(992―1057),字明复,是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春秋》学者之一。他早年曾多次应试不中,后退居泰山,研习《春秋》,著书讲学,学者称其为泰山先生。孙复退居泰山,但并不是隐者。他依然心系国家,关心朝政,其学术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的意味。孙复高足石介曾作《明隐篇》曰:“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其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栗,盖有所待也。”[8]孙复之后受到范仲淹、富弼的推荐在朝廷有所任职,然他“所待者”绝非仅此,还应该包括他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所表露的政治理想。从书的篇名中就可以看出孙复对《春秋》主旨的思考,即对王权的极度推崇。孙复在解释《春秋》的过程中尤其关注礼制之事,他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彰显王权。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二、挺立王权:孙复的《春秋》观念
欧阳修曾经评价孙复的《春秋》学说:“(孙明复)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9]欧阳修指出了孙复《春秋》学的两个特点:其一为“不惑传注,不为曲说”,这是指孙复的解经之法,以经为主,不曲从前人所作传注;其二为“考时之盛衰以推见王道”,这是孙复对《春秋》之写作本意的认识,即对《春秋》的写作意图或者基本性质、基本精神的认识。这是历代学者研治《春秋》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孙复从当时实际出发,通过对诸侯的褒贬来阐明王道理想,正符合《春秋》之本义。 (一)“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的解经之法
孙复的解经之法受到了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所开启的“舍传求经”之风的影响。啖助认为三传各有侧重、各有所失,未能达乎《春秋》大宗。“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10]儒学在西汉时被定为一尊之后,经师们严守师法、家法,注重经说的师承传授,致力于章句注疏之学。囿于门户之见,他们各守一传,不肯相通,甚至对于其他的传注进行抨击,但基本没有人对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从整体上进行批评。南北朝时期,在经学的阐释性著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义疏,这是汉代经注、经说的发展。对于前人的传注、义疏之学,啖助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主张以“理”通之。他说:“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10]啖助所谓“理”,是指《春秋》的宏旨大义,主张从整体上阐明《春秋》。啖助等人对春秋三传以及历代注疏的批判,试图将人们从传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研治经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孙复基本承袭了啖、赵、陆三家的说经之法,他自觉地站在三传及前人注疏之外来对《春秋》经说进行审视、分析和阐发。他在与范天章的一封书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11]孙复的“不惑传注”在其《春秋尊王发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桓公十五年有经云:“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对此事的看法完全一致,都是认为周王“非礼”。①孙复则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者,诸侯贡赋不入,周室材用不足也。”[12]孙复将此事的根源归结为诸侯身上,从而转移了周王“非礼”的责任,这同时也体现了他尊王的立场。
历代《春秋》学者对《春秋》经义的研究和发挥构成了《春秋》学的发展过程。他们在吸收已有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对于《春秋》经义的理解与阐释。同样,孙复“不惑传注”并非指他对传注完全排斥,而是断以己意,取精用宏。孙复也继承了三传的某些特点,如他也接受《谷梁传》之“日月时例”之说:“《春秋》之法,恶甚者日,其次者时,非独盟也。以类而求,二百四十二年之诸侯罪恶轻重之迹,焕然可得而见矣。”[13]因此可以说,孙复首先是通过对三传及先儒的说法进行通盘了解后,才依据其个人立场和认知作最后的评断与取舍,而判断与取舍的标准即在于是否合乎《春秋》经义和孔子大义,尤其注重在“尊王”大义的发挥上。
(二)挺立王权:孙复对《春秋》写作意图的思考
关于《春秋》的写作意图,啖助以为是“救时之弊,革礼之薄。”[10]赵匡则说:“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故凡郊庙、丧祭、朝聘、?狩、昏取,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10]依赵匡之意,《春秋》的宗旨乃是阐明王道,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违背常典、礼制的事情,《春秋》“则讥之”,其目的是为了防乱,“礼典者,所以防乱耳”;而对于常典所没有涉及的非常之事,《春秋》则通过“权变”以进行褒贬,“裁之圣心”以“相助救世”。”赵匡对于《春秋》写作意图的思考以及对于兴常典和著权制两方面的分析,在孙复那里得到了明显的承袭,石介在追忆其师研习《春秋》的用心时说:
先生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14]
可见,孙复也注重《春秋》经世致用的功能,将其视为“治世之大法”。其中,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是,孙复将“尊王之义”突出到了《春秋》大义的首位。孙氏认为春秋时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王”。他在《春秋尊王发微》开篇解“元年春王正月”时说:“《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至《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黍离》是《诗经?王风》的首篇。《毛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5]西周时,周王强盛,政教加于诸侯,其统治力及于天下诸国。然东迁之后,周王失去了原来的宗主地位,而与诸侯齐列,故其诗也降为国风,即孙复所谓“《诗》自《黍离》而降,天下无复有雅”,也正反映出春秋时期王权的衰落。《文侯之命》乃是《尚书》中的一篇。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之后,其太子宜臼和庶子余臣分别被立为“平王”和“携王”。晋文侯于公元前760年执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诰在西周时是周王以大义谕众或者告诫臣工的文书,如《尚书?周书》载有《大诰》、《汤诰》、《康王之诰》等篇。东迁之后,周王的统治力下降,其诰命的有效性也随之减弱,甚至逐渐流于形式,即“天下无复有诰命也”。孙复进而解释《春秋》为何自隐公始,他说:
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13]
这是孙复所描绘的春秋时期的无王状态。平王东迁之后,由于王室势力衰微,不仅无法号令诸侯,甚至有时还需要寻求诸侯的庇护与支持。没有周王的约束,各诸侯国以力相逐,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礼法不修、政治不明,甚至“征伐四出,荡然莫禁”。“是时纪纲既绝,荡然莫禁,孔子惧万世之下,乱臣贼子交轨乎天下也,故以圣王之法从而诛之。”[13]在古代社会,君主是政权的核心,而政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孙复看来,“无王”是一种极坏的状态。孔子作《春秋》即是针对这种天下无王的政治社会情境。 三、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孙复对《春秋》礼典的阐释
王权与礼典制度密不可分,二者互为表里。天子制定的祭祀、继承、朝觐、盟会制度,乃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王权乃是礼典制度得以有效执行的前提和保障。当王权式微、无力维持的时候,礼典制度也就成为僭越者僭越的对象。欧阳修曾经对五代时期的社会作过如下评述:“夫礼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16]春秋时期的社会情境与五代时期甚为相似,各诸侯国悖礼擅权之事屡见不鲜。《春秋》经传中涉及了相当多的礼制问题,如祭祀、继承、朝聘、盟会等,范围相当之广,其大类可以分为宗庙之礼、朝廷之礼、人鬼之礼。宗庙之礼主要指天子或诸侯自身政权所需的礼制,如即位、继承、昏礼等;朝廷之礼则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涉及权力分配与运行的礼制,如征伐用师、朝觐、盟会等;人鬼之礼主要指祭祀之礼,如祭天、祭宗庙等“常祭”或非常时期的“时祭”(如祭雨等)。以《春秋》议礼,进而以礼议政乃是学者表达自身政治观念的重要途径。孙复严格按照王权政治理念对《春秋》所载礼典之事进行阐释。
(一)宗庙之礼。在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即位与继承制度乃是关系政权延续与稳定的重要保证。孙复认为,诸侯即位乃一国之大事,必须以王命为首要依据,自行即位或为众所拥戴即位即为不正。如他说:“隐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书即位,以见正焉。”[13]隐公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按周朝的传统礼法,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由于惠公死时太子姬允(即鲁桓公)幼小,于是由庶长子隐公摄政,并非正式继承君位。而孙复认为隐公由于得到了王命的支持,其继承惠公君位乃是正当的,并无不合理之处。隐公四年,弑君篡位的卫前废公州吁由于穷兵黩武、众叛亲离而被诛,卫桓公之弟晋则受到国人的拥戴而被众大夫立为宣公。可以说,宣公即位乃是符合民心,孙复却认为“不正”,他说:“诸侯受国于天子,非国人可得立也,故曰‘卫人立晋’,以诛其恶。”[13]可见,孙复在此依然将王命而非民心作为君主即位正当与否的首要依据。但是由于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之间因继承问题而产生的纷争甚至流血事件数不胜数。在王命不行的社会环境中,孙复同样遵循传统的立嫡继统原则,他说:“为国之道,莫大于传嗣,传嗣之道,莫大于立嫡。所以防生乱而杜篡夺也,用能尊统传绪,承承而不绝。”[17]不仅是涉及政权延续的即位或继承问题,王后问题同样关系到政权稳定,“是时文姜乱鲁,骊姬惑晋,南子倾卫,夏姬丧陈,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举也。”[12]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相互嫁女联姻相当普遍,而往往与政治事件相联系,孙复对此甚为警觉。所以他对诸侯之间的婚礼亦极为重视,“王后,天下母,取之、逆之皆天子命,非人臣可得专也。”[12]亦可见其尊王立场。
(二)朝廷之礼。王权乃是大一统政治格局的中心和等级社会稳定的保障,如果天下无王,那么政权分散必然导致政局动荡,天下不安。由于周王势力衰微,于是各诸侯国纷纷以力相持,互相征伐不断。“夫礼乐征伐者,天下国家之大经也,天子尸之,非诸侯可得而专也。诸侯专之犹曰不可,况大夫乎!吾观隐、桓之际,诸侯无小大皆专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无内外皆专而行之,其无王也甚矣,故孔子从而录之,正以王法。”[13]征伐用师的命令本来只能由天子发出,而春秋时期,诸侯无大小皆专而行之。在孙复看来,孔子正是通过春秋笔法进行贬斥,以明其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诸侯之间的盟会开始盛行,孙复对此极力贬斥。他说:“盟者,乱世之事,故圣王在上阒无闻焉,斯盖周道陵迟,众心离二,忠信殆绝,谲诈交作,于是列国相与是有歃血要言之事尔,凡书盟者,皆恶之也。”[13]孙复确实道出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盟会盛行的原因。孙复对诸侯之间盟会的指责还有其他原因,如他说:“诸侯守天子之土,非享觐不得逾境。”[13]古代王权政治一直盛行着这样的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担负着守护天子之土的职责,若无天子之命而私自逾境会盟则是对天子权威和礼法等级制度的践踏。这是推崇王权的孙复所不能容许的。
(三)人鬼(祭祀)之礼。祭祀在中国古代王权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祭祀是它的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巩固的措施和宣示的手段。一个政权通过各类祭祀活动建立与各种神灵、大地山川的隐秘的、神意的关联,从而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18]隐公五年,仲子(惠公夫人,桓公之母)之庙落成。隐公在主持仲子神主入庙的祭祀时,献六羽乐舞,即经云“初献六羽”。对此,孙复说:“初,始也,舞者所执大雉之羽也。其言初献六羽者,鲁僭用天子之乐,舞则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此减用六羽以见其僭天子之恶。且经言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则群公皆用八佾可知也。”[13]六羽即六佾。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这里尤其需要注意“初”的意义,初即始,此处言鲁国于仲子之祭始用六佾。按春秋常事不书的习惯,孙复推知鲁国在其他处乃行八佾。因此,此处乃是贬斥鲁以诸侯之位而僭用天子祭礼。《春秋》经记载桓公曾于桓公五年行“大雩”。“雩”是春秋时期一种用来求雨的祭祀制度,“大雩”则是雩于上帝者,是天子之祭。对于诸侯而言,只能雩于山川百神。因此,桓公行“大雩”违背了祭祀之礼,是一种僭越的行为。孙复于是感叹:时周室既微,王纲既绝,礼乐崩坏,天下荡荡,诸侯之僭者多矣。”[12]
需要指出的是,孙复的王权政治理念所维护的乃是天子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以及围绕王权所设定的礼制、典章等制度,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位君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兽之道也,人理灭矣。”[17]对于僭越天子之礼的诸侯,孙复毫不犹豫的进行贬斥;对于违背为君之道的天子,他也并不为之讳。如庄公元年,经云:“单伯逆王姬”。孙复解释说:“鲁桓见杀于齐,天子命庄公与齐主婚,非礼也。庄公以亲雠可辞,而庄公不辞,非子也。故交讥之。”[19]鲁庄公与齐国有弑亲之仇(指鲁桓公被杀于齐),而天子却命鲁庄公与齐主婚,孙复认为此乃“非礼”,庄公接受这一原本可以推辞的命令,同样没有尽到自己为人子的责任。可见,孙复对于周天子的批评还是比较委婉的。 四、著权制以辨华夷:对礼的有效补充
在孙复看来,“无王”乃是春秋时期政治状态和社会情境的基本特征。王权的凋零首先表现在春秋时期诸侯、大夫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的凌夷,如前述,孙复主要通过兴常典的方式对此进行指责。然而,春秋时期存在着诸多礼制、典章无法规范的“非常之事”。在孙复看来,春秋时期非常之变最巨者即是夷狄乱华。孙氏对整个春秋时期进行了总结。
天子失政,自东迁始,诸侯失政,自会?梁始。故自隐公至于?梁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自?梁之会,至于申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专执之。自申之会,至于获麟,天下之政,会盟征伐,吴楚迭制之。圣王衔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周道沦胥,逮此而尽。[20]
孙复将春秋时期划分为三个时期,其实这只是相对而言,诸侯、大夫的专权以及夷狄对华夏的入侵充斥于整个春秋时期。孙复在此并不是表达一种时间先后的顺序,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周道沦胥”以致“扫地而尽”的过程。天子失政,诸侯、大夫擅权专政乃是诸夏内部的冲突与争夺,所侵犯的乃是天子的权威,破坏的是宗法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等级制度。夷狄对中国的侵夺则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威胁,孙复对此尤为注意。“东迁之后,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乱中国,盗据先王之土地,戕艾先王之民人,凭陵寇虐,四海汹汹,礼乐衣冠尽扫地矣。其所由来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国失道故也。”[21]华夷之辨实是孙复王权政治理想的有效补充。孙复一方面对四夷侵攘土地、戕害人民、破坏礼义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谴责,所以他对齐桓、晋文的攘夷之功甚为推崇。另一方面,他将夷狄乱华的由来归诸中国失道,齐桓、晋文之攘夷也仅是一时之功。“召陵之盟、城濮之战虽然迭胜强楚,不能绝其僭号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兴起如宣王者,则是时安有齐威、晋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21]在孙复看来,若要恢复传统的华夷关系,必须重振王道。然政治社会的发展却是,自齐桓、晋文之后,“诸夏不振,丧乱日甚,幅裂横溃,制在荆蛮故也。自是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荆蛮迭制之。”[22]
楚国乃是“夷狄之钜者”。楚灵王在位时,分别于鲁昭公八年、十年灭陈、灭蔡;而继位的楚平王为了与诸夏修好,于鲁昭公十三年恢复陈、蔡二国。对此,孙复提出自己的疑问:善与非善?他从中看到的乃是:“圣王不作,诸侯不振,二国之命,制在荆蛮故也。孔子以陈蔡自归为文,所以抑强楚而存诸夏也。”[22]陈、蔡二国由于势力衰微,已经无法自存,完全为楚国所制。面对这样的事实,孔子只能“以陈蔡自归为文”,从记事方式上做文章,而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乃是“抑强楚而存诸夏”这一深层价值观念。
孙复并非对夷狄进行绝对的贬斥,也有一定的褒扬。夷狄之另一钜者乃是吴国。关于吴国,定公四年有一段记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孙复解释说:
吴称子者,大救蔡也。晋合十八国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吴能救之伐之,此吴晋之事,强弱之势,较然可见也。故自是诸侯大小皆宗于吴……吴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败,长驱入郢,夷其宗庙,坏其公室,此则甚矣,故曰“庚辰,吴入郢”,反狄之也。[23]
首先,此时吴国国势强盛,已经超越传统强国晋国,“诸侯大小皆宗于吴”。其次,吴国以己之力救蔡伐楚,善也,《春秋》称其爵以褒之。第三,吴国乘楚国囊瓦之败,长驱入郢,夷其宗庙,坏其公室,乃是夷狄之道,《春秋》称“入”以贬之。如果吴能够尊重华夏诸国,修礼讲睦,孙复同样用褒义。这也是孙复所一直希望的一种状态。然而,吴楚两国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往往以自身意愿行事。吴国在春秋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中原诸侯不能小觑的强大力量。对此,孙复也只能在表达自己对夷狄僭越的不满的同时,感叹对“圣王不作、名分失正”的无奈。在孙复看来,孔子作《春秋》的立意就是要突出“尊王”,所以,在论述《春秋》的另一要义“攘夷”时,他也以“尊王”来贯通之。[24]
在孙复看来,不仅仅是长期被视为夷狄的楚国,华夏之国如果见利兴战,则形同夷狄。如鲁文公十年夏,秦伐晋,孙复的态度非常明确。“晋自令狐之战,不出师者三年,其厌战之心亦可见也。而秦不顾人命,见利则动,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晋’以黜之。”[2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复对晋的同情和对秦见利而动的憎恨、不满,斥之为“夷狄之道”。又,成公三年,“郑伐许”,孙复解释为:“其曰郑伐许者,狄之也。狄之者,郑襄背华即夷,与楚比周,一岁而再伐许,故狄之也。”[26]“背华即夷”是说华夏诸国如果背离礼乐文明,则当以夷视之。华夷之辨的文化渊源相当久远,有关的辨析涉及种族之别、地域之别、习俗之别、贵贱之别等,其核心乃是精神文化之别,即道德文明之别。这也是孙复在华夷之辨中所遵循的尺度。
五、影响与评价
孙复的《春秋》学在北宋时期影响甚大,程颐曾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27]
孙复《春秋》学之所以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他“不惑传注”的解经方式。虽然中唐时期的啖助、陆淳已经开启了“舍传求经”之风,但其实力并不足以和当时《五经正义》的官学相抗衡,未能成为主流。以致宋初经学仍沿袭汉唐注疏之学,无甚创新,如皮锡瑞所谓:“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28]所以孙复取诸卓识绝见、重为春秋注解实具有破除藩篱、开启新风的思想史意义。自此,疑传、疑经、变古成为宋代研治经学的主流。如孙复高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说:“左氏、公羊氏、谷梁氏,或亲孔子,或去孔子未远,亦不能尽得圣人之意。至汉大儒董仲舒、刘湘,晋杜预,唐孔颖达,虽探讨甚勤,终亦不能至《春秋》之蕴。”[29]欧阳修不仅对孙复解经之法表示赞同,他自己在评论《五经正义》时说:“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30]可以发现,北宋学者致力于摆脱汉唐以来重视名物训诂的章句注疏之学,主张从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出发,开辟了研治经学的新途径,进而开创出符合时代和思想发展的义理之学。 孙复对传统的《春秋》学理论进行改造,将“尊王之义”推为《春秋》大义的核心。在《春秋尊王发微》中,他极力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处处体现出对于王权政治的推崇。漆侠先生曾经指出,孔夫子极力歌颂和维护周天子的高大形象,但就历史的实际来看,孔夫子所描绘的周天子不过是一个理想和期望而已;而对于孙复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北宋皇帝具备了孙复所论述的礼乐、刑政、赏罚等权力。[31]的确,同周天子相比,北宋皇帝确实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高的统治力,漆先生的论述不无道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宋前期的政权同样面临着深重的内忧与外患,甚至比东周时期更为严峻。历经了唐代藩镇之割据以及五代的战乱之后,天下初定,地方上仍存在着较强的分裂势力;同时,北方辽国、西北西夏均占地极广,势力足以与赵宋相匹敌,且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屡屡入侵。可以说宋朝具有比前代更为严重的外患问题。宋朝的政治形态以中央集权为其特色之一,即以强干弱枝为基本国策。此一国策既要求将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使君权大为提升,同时要求在思想意识上推崇王权的政治理念。“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当道,君正而国定矣。”[27](1218)“孙氏尊王之论,足为宋人中央集权制张目。”[32]赵伯雄指出,唐朝的啖、赵、陆三家,就已有了改造《春秋》学的意识,但他们的改造,似缺乏明确的宗旨。孙氏基于对历史经验以及时政的理解,首揭“尊王”的大旗,把一部《春秋》改造成了处处维护天子权威、严厉谴责犯上行为的经典。[33]孙复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于《春秋》的解读,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北宋政权建设的需要。
作为礼的有效补充,孙复对华夷关系的论述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共鸣。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辨。”[27](1114)宋代另一位重要的春秋学者胡安国也说:“《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34]“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34]这与孙复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立场是一致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孙、胡二氏奠定了宋代春秋学的主流。
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事者,几可谓无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御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无论与孙复、胡安国有出入否,故无不受二氏之影响者;亦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32](141)
如前文所述,对礼的重视是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孙复同样重视礼典与王权的的关系,并采取了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的方式以表达其王权政治理想。宋代学者有重礼的风气,欧阳修说:“夫礼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35]司马光也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36]后世也有学者从礼学出发来评价孙复的思想,如叶梦得说:“孙明复《春秋》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自?牾,有甚害于经者。虽盖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37]叶氏正是站在礼学的视角对孙复进行批评,主要是针对孙复“不能尽礼之制”。客观来讲,叶氏的批评自有其道理。孙复以己意说经,对《春秋》中所涉及的祭祀、继承、朝聘、盟会等礼制典章自不能详加考证,甚至有所?牾,然而对孙复的评价还应该结合他的写作意图。朱熹评价说:“近时言《春秋》,皆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38]正如前文所述,面对春秋时期周王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孙复通过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的方式来表达尊王大义,即叶氏所述“以礼论当时之过”。朱熹虽然同样认为孙复“未能深于圣经”,但他从义理出发,指出孙复通过《春秋》而“推言治道”,却也符合孙复思想的实际。
注释:
①《左传》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公羊传》同样认为是讥周王,“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谷梁传》的解释为:“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可见,三传都认为此处是讥周王非礼。